Cell:“冰桶挑战”的回响——当“基因神药”抵达大脑,为何ALS的恶魔仍在狂欢?
来源:生物探索 2025-08-29 09:12
这项研究清晰地揭示了脑脊液中的药效学标志物(如poly(GP))与大脑组织中的核心病理改变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脱节。一个看似“漂亮”的生物标志物数据,并不总能转化为真实的临床获益。
大约十年前,一场名为“冰桶挑战”(Ice Bucket Challenge)的活动席卷全球,它以一种独特而冰冷的方式,让一个罕见的疾病——肌萎缩侧索硬化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渐冻症”,走入了公众的视野。这是一种残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逐渐剥夺患者的运动能力,将鲜活的灵魂禁锢在日渐僵硬的躯体中。面对这个医学难题,全球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不懈地探索治疗方法,其中,针对疾病根源的基因疗法无疑是最令人期待的曙光之一。
在所有ALS病例中,一个名为 C9orf72 的基因突变是最常见的遗传原因。这个突变的特点是在基因的非编码区出现了一段“GGGGCC”六核苷酸序列的异常重复扩增。这些多余的、如同“口吃”般的遗传密码,会转录出有毒的RNA,并进一步被翻译成有毒的二肽重复蛋白 (Dipeptide Repeat Proteins, DPRs)。它们像幽灵一样在神经元中肆虐,扰乱细胞的正常功能,最终导致运动神经元的死亡。
针对这一明确的“病根”,一种名为反义寡核苷酸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 ASO) 的疗法应运而生。它的原理就像是为这段错误的基因序列量身定做的“精准导弹”。其中一款名为BIIB078(通用名 tadnersen) 的ASO药物,被设计用来专门识别并摧毁携带“GGGGCC”重复序列的信使RNA (mRNA),从而从源头上阻止有毒蛋白的产生。在临床前的动物实验中,它展现了巨大的潜力,点燃了无数患者和家属的希望。然而,在真实世界的人体临床试验中,这款被寄予厚望的药物却未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最终因缺乏疗效而宣告终止。
一个充满希望的疗法为何会折戟沉沙?当“精准导弹”已经发射,它是否准确击中了目标?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8月26日,《Cell》的研究报道“Molecular impact of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 therapy in C9orf72-associated ALS”,对这次“失败”的临床试验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分子“尸检”。研究人员通过分析接受BIIB078治疗的ALS患者在治疗期间和去世后捐赠的宝贵样本,为我们揭示了药物在人体内的完整旅程,以及它与我们身体之间发生的复杂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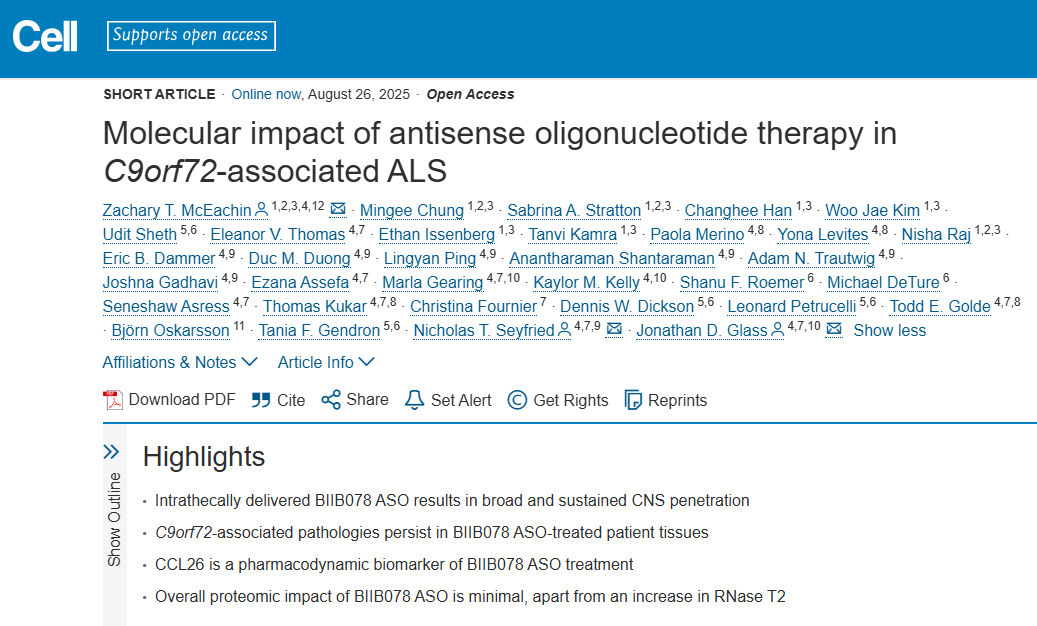
迷雾中的信使:药物在“生命之水”中的起伏之旅
要了解一种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是否起效,研究人员首先会将目光投向脑脊液 (Cerebrospinal Fluid, CSF)。脑脊液,被誉为“生命之水”,它环绕着我们的大脑和脊髓,不仅提供物理缓冲和营养,更像是一个信息丰富的“情报站”。通过分析脑脊液的成分变化,我们可以窥探大脑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子事件,而不必进行创伤性的脑组织活检。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检测了脑脊液中一种关键的药效学生物标志物——poly(GP)二肽重复蛋白的水平。这种蛋白是C9orf72基因异常扩增的直接产物,它的含量高低,可以直观地反映出ASO药物是否有效地抑制了致病基因的表达。这就像是评估一场灭火行动时,我们不去直接看消防员,而是去测量火场中的烟雾浓度。
结果显示,BIIB078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六名可供分析的患者中,有五名的脑脊液中poly(GP)水平在治疗后出现了下降,平均降幅达到了37.2%。这表明,药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它的靶标。然而,这个结果并非一个简单的“好消息”。数据的细节揭示了更为复杂的现实。
首先,这种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和不稳定性。例如,其中一位代号为#6的患者,表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响应:其poly(GP)水平呈现出持续而稳定的下降,最终降幅高达77.4%。这无疑是研究人员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其他患者的反应则充满了波动,poly(GP)水平时而下降,时而又有所回升。这种不稳定的药效,不禁让人心生疑虑:这种程度的靶标抑制,是否足以扭转疾病的进程?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研究人员接着测量了BIIB078药物本身在脑脊液中的浓度。他们发现,在所有患者中,药物在初期的“负荷剂量”阶段(即为了让药物浓度快速达到稳定水平而进行的密集给药)后,脑脊液中的浓度会迅速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则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轨迹。有趣的是,那位poly(GP)下降最显著的#6号患者,是唯一一位在后续的维持治疗中,脑脊液药物浓度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的。
那么,是不是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越高,治疗效果就越好呢?研究人员将药物浓度和poly(GP)水平进行了关联性分析。结果再次出人意料:在大多数患者中,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线性关系。只有在#6号和#5号患者身上,才观察到了中度到强度的相关性(R²=0.51)。这意味着,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我们在脑脊液这个“情报站”里看到的药物浓度,并不能完全预测它在大脑这个“主战场”里的实际战绩。脑脊液这扇窗户,似乎蒙上了一层迷雾。它告诉我们信使(药物)已经出发,但信使的旅程充满了起伏,它能否以及如何将信息传递到每一个需要它的角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风暴的预警:当免疫系统被“外来客”唤醒
当一种外来物质,即便是为了治疗疾病而设计的药物,进入我们高度精密的人体系统时,总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枢神经系统(大脑和脊髓)过去常被认为是“免疫豁免”的区域,意味着它在很大程度上与身体其他部位的免疫系统隔绝,以保护其脆弱而关键的功能。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知道这种豁免并非绝对。ASO药物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核酸链,它能否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任务,而不惊动中枢神经系统里警惕的“免疫哨兵”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名为NULISA的超灵敏蛋白质检测技术,对患者治疗前后的脑脊液样本进行了全面扫描,分析了数百种与免疫和炎症相关的蛋白质。这就像是对战场通讯进行全频段监听,希望能捕捉到任何异常的信号。
监听的结果令人警醒。数据显示,在接受BIIB078治疗后,患者的脑脊液中多种促炎细胞因子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和相关的受体水平出现了显著且持续的升高。这表明,BIIB078的进入,并非一次悄无声息的潜入,而是在中枢神经系统内部,明确地触发了一场免疫应答。
在所有被激活的免疫信号中,一个名为“C-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26” (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26, CCL26) 的蛋白尤为突出。它的升高最为稳健和一致,在所有患者、所有时间点上都清晰可见。这种升高发生在药物的负荷剂量阶段之后,并且在整个维持治疗期间都保持在高位,即便后续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开始下降,CCL26的水平也并未随之回落。
为了确保这一发现不是由操作本身(如反复的腰椎穿刺)引起的,研究人员巧妙地利用了临床试验的设计。部分患者在进入药物治疗组之前,曾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安慰剂注射。对这些安慰剂治疗期样本的分析显示,CCL26的水平保持稳定。这一对比有力地证明了,CCL26的升高是BIIB078药物本身引发的特异性反应,而非治疗过程中的非特异性影响。
这一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首次在人类临床试验中,明确揭示了鞘内注射ASO药物可以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引发持久的免疫反应。CCL26,这个原本在过敏性疾病中研究较多的趋化因子,如今成为了一个潜在的、用于监测ASO疗法免疫反应的生物标志物。
然而,这个免疫风暴的预警信号,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更为深刻的问题。这场由药物引发的免疫反应,对ALS的病理进程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好是坏,抑或仅仅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副作用?它是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药物抑制靶标基因所带来的潜在益处?甚至,它会不会本身就是导致临床试验失败的“帮凶”之一?这项研究无法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发出的这个明确信号,无疑为未来所有旨在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基因疗法,敲响了警钟。未来的药物研发,不仅要关注“疗效”,更要深入理解并妥善管理药物与人体免疫系统之间这场复杂的“对话”。
抵达“犯罪现场”的侦探:为何元凶依然逍遥法外?
脑脊液中的发现固然重要,但它终究只是间接证据。要真正评判BIIB078的成败,我们必须深入疾病的核心——大脑和脊髓组织,也就是这场战斗的“主战场”。感谢那些在生前决定捐献自己身体的伟大患者,研究人员得以在他们去世后,对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组织进行细致的分子病理学分析。这使得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观察到药物分布的最终版图,以及它对疾病核心病理的真实影响。
第一问:药物是否抵达了战场的每一个角落?
答案是肯定的。通过巧妙的免疫组织化学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和原位杂交 (in situ hybridization, ISH) 技术,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成功“看到”了BIIB078药物分子的身影。结果显示,药物广泛地分布在整个中枢神经系统,从脊髓的运动神经元,到大脑皮层、海马体、基底节等多个关键区域,都能检测到药物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药物不仅停留在细胞外,还成功地进入了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内部,抵达了它需要发挥作用的场所。
然而,药物的分布也并非均匀且永久。研究人员发现,组织中的药物浓度与最后一次给药到去世的时间间隔密切相关。在最后一次给药后仅17天就去世的患者(#1号)组织中,可以检测到非常强烈的药物信号;而在间隔长达455天后去世的患者(#6号)组织中,药物信号则变得非常微弱。这表明,尽管BIIB078能够广泛渗透,但它在组织中的半衰期是有限的,需要持续给药才能维持有效浓度。
第二问:药物是否有效减少了“敌人”的武器(有毒RNA)?
既然药物已经到位,那么它是否成功完成了其首要任务——降解有毒的C9orf72信使RNA?研究人员通过定量PCR (qPCR) 等技术对组织中的RNA水平进行了精确测量。结果显示,BIIB078的效果只能用“温和”来形容。在药物浓度最高、给药间隔最短的几位患者的脊髓组织中,确实观察到了致病的C9orf72转录本(V1和V3变体)水平的显著下降。这再次证明,只要浓度足够,BIIB078确实能够发挥其设计的分子功能。然而,在其他患者或药物浓度较低的脑区(如运动皮层),这种抑制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甚至没有统计学差异。
第三问:也是最关键的一问,药物是否清除了疾病的“核心罪证”(病理蛋白聚集)?
这是评判整个疗法成败的终极标准。ALS,尤其是由C9orf72突变引起的ALS,其神经元死亡的直接执行者,是那些由异常RNA翻译而来的有毒二肽重复蛋白(DPRs),以及另一种名为TDP-43的蛋白的异常磷酸化和聚集 (phosphorylated TDP-43, pTDP-43)。如果BIIB078疗法有效,我们理应看到这些“核心罪证”在治疗后被显著清除或减少。
然而,显微镜下的景象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否定的答案。
无论是在脊髓的运动神经元中,还是在大脑皮层的神经细胞里,大量的poly(GP)和poly(GA)蛋白包涵体依然存在,其形态和数量与未接受治疗的c9ALS患者相比,并无二致。同样地,作为ALS更广泛的病理标志,pTDP-43的异常聚集也丝毫没有得到改善。
为了让证据更具说服力,研究人员甚至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双重染色实验。他们将显示BIIB078药物的信号和显示有毒蛋白(poly(GA))的信号在同一张组织切片上进行标记。结果清晰地显示,在同一个神经元细胞内,BIIB078药物分子(“侦探”)和poly(GA)蛋白包涵体(“罪犯”)可以同时存在。
这一发现,是整个研究中最核心、也是最令人扼腕的部分。它说明:药物虽然成功抵达了犯罪现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新的犯罪工具(有毒RNA)的生产,但它对于已经存在于现场的、由过去罪行累积下来的大量物证(蛋白聚集物),却显得无能为力。
这个结果深刻地揭示了脑脊液生物标志物与组织病理之间的巨大鸿沟。尽管我们在脑脊液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poly(GP)下降,但这一下降并未转化为组织层面病理状态的真正逆转。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患者的临床症状没有改善。对于像ALS这样的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临床症状出现时,神经元内可能已经积累了大量难以清除的“垃圾”。仅仅切断“垃圾”的新来源,可能已经为时已晚。未来的治疗策略,或许需要“开源”与“截流”并举——既要阻止有毒蛋白的产生,也要找到方法清除已经形成的蛋白聚集体。
蛋白质世界的“涟漪”:一次治疗在细胞深处留下的“分子指纹”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BIIB078治疗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深远影响,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蛋白质组学 (Proteomics) 分析。他们利用先进的质谱技术,对来自BIIB078治疗患者、未经治疗的c9ALS患者以及健康对照者的脊髓组织样本中数千种蛋白质的丰度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和量化。这就像是为每一个样本绘制了一幅详尽的“分子肖像画”,通过对比这些肖像画的异同,来发现治疗带来的细微变化。
如果BIIB078能够有效地逆转疾病,我们期望看到的景象是:经过治疗的患者,其脊髓组织的“分子肖像画”应该会从“疾病状态”向“健康状态”回调。然而,分析结果再次印证了此前的病理学观察。BIIB078治疗组的蛋白质组学特征,与未经治疗的c9ALS组高度相似(相关性系数R高达0.8),两者都与健康对照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具体来说,在c9ALS患者(无论是否接受治疗)的脊髓中,都普遍存在着反映神经元丢失和神经胶质细胞(包括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过度激活的标志性蛋白变化。这表明,BIIB078治疗并未能在宏观的蛋白质网络层面上,纠正ALS的核心病理过程。疾病的分子基础依然顽固。
然而,这幅复杂的“分子肖像画”并非毫无波澜。当研究人员将目光从全局转向细节,寻找那些专门对BIIB078药物产生响应的蛋白质时,两个意想不到的名字跃然纸上:核糖核酸酶T2 (Ribonuclease T2, RNase T2) 和脱氧核糖核酸酶II (Deoxyribonuclease II, DNase II)。
在BIIB078治疗组的脊髓组织中,这两种核酸降解酶的水平显著高于未经治疗的患者和健康人。更引人注目的是,它们的丰度与组织中BIIB078药物的浓度呈现出惊人的正相关性——药物浓度越高,这两种酶的水平就越高,相关性系数R值双双达到了0.96。这是一种极强的关联,几乎可以肯定,这两种酶的“异动”是细胞为了应对BIIB078药物而产生的直接反应。
这一发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侦探方向。RNase T2和DNase II都是溶酶体 (lysosome) 中的关键水解酶,而溶酶体是细胞内的“垃圾处理中心”和“回收站”。此前的研究已经知道,ASO药物在进入细胞后,很多都会被运输并聚集在溶酶体中。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细胞是否将BIIB078识别为一种外来的、需要被清除的“核酸垃圾”,因此上调了溶酶体内的相关降解酶(如RNase T2),试图将其分解掉?
这个“分子指纹”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细胞与ASO药物之间一场不为人知的“暗战”。细胞并非被动地接受治疗,而是在主动地感知、响应甚至试图对抗这种外来的治疗分子。理解这场“暗战”的规则和后果,对于优化未来的ASO药物设计至关重要。
溶酶体内的猫鼠游戏:当“降解大师”遇到“变形金刚”
基于蛋白质组学的线索,研究人员将焦点锁定在了RNase T2与BIIB078的直接互动上。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体外实验,试图重现并解析这场发生在细胞“垃圾处理中心”——溶酶体内的“猫鼠游戏”。
第一回合:猫(RNase T2)能抓住并吃掉老鼠(BIIB078)吗?
研究人员首先测试了RNase T2是否能够降解BIIB078。ASO药物为了在体内保持稳定,通常会进行各种化学修饰,BIIB078也不例外。它的RNA“两翼”被加上了2'-O-甲氧乙基 (2'-O-methoxyethyl, 2'-MOE) 的化学基团,就像是给“老鼠”穿上了一层坚固的盔甲。实验结果显示,这层盔甲非常有效。当BIIB078与有活性的RNase T2一起孵育时,它几乎毫发无损,表现出强大的抵抗力。作为对比,一段没有任何化学修饰的、序列与BIIB078相似的RNA,则被RNase T2迅速切碎。这表明,BIIB078这位“不速之客”虽然被送进了“垃圾处理中心”,但它本身的设计使其能够抵抗“降解大师”的分解。
第二回合:老鼠(BIIB078)会不会反过来牵制住猫(RNase T2)?
既然无法被降解,那么BIIB078是否会与RNase T2发生其他形式的互动呢?研究人员利用生物膜干涉技术 (Bio-layer interferometry, BLI) 测量了两者的结合能力。结果令人惊讶:BIIB078能够与RNase T2非常紧密地结合,其亲和力常数(Kd)达到了23.8纳摩尔(nM)级别,这是一个相当强的相互作用。
这个发现立刻引出了一个新的假设:如果BIIB078紧紧地“抱住”了RNase T2,它会不会像一个“绊脚石”,影响RNase T2去执行其正常的生理功能——降解其他RNA底物?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竞争性切割实验。他们先将RNase T2与不同浓度的BIIB078预孵育,让它们充分结合,然后再加入一种能够被RNase T2降解并产生荧光信号的RNA底物。结果清晰地显示,随着BIIB078浓度的增加,RNase T2降解荧光底物的效率被显著抑制了。
至此,这场“猫鼠游戏”的全貌浮出水面:
1. 细胞侦测到大量外来的ASO(BIIB078),启动防御机制,上调了溶酶体中的降解酶RNase T2(猫),试图清除这些“入侵者”。
2. 然而,BIIB078由于其特殊的化学修饰(盔甲),对RNase T2的降解具有抵抗力,“猫”无法吃掉“老鼠”。
3. 更进一步,BIIB078会反过来与RNase T2紧密结合,像“牛皮糖”一样缠住它,从而抑制了RNase T2对其他正常RNA底物的切割活性。
这场发生在微观世界里的复杂互动,再次凸显了我们对ASO药物在细胞内行为的理解仍有不足。药物的上调了RNase T2,这本身可能是一种细胞应对药物负荷的代偿性反应,但药物反过来又抑制了该酶的功能,这种负反馈调节的长期生物学后果是什么?这是否会对细胞的正常功能,特别是溶酶体的稳态,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些都是此次“失败”试验留给我们的宝贵思考题。
从一次“失败”中汲取的深刻教训
BIIB078的临床试验,从结果上看无疑是失败的。它未能延缓ALS患者的疾病进展,未能给这个饱受折磨的群体带来希望。然而,这项发表于《细胞》的深入研究,却将这次失败转化为了一座知识的富矿,为整个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领域提供了几点至关重要的教训:
第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生物标志物的意义。这项研究清晰地揭示了脑脊液中的药效学标志物(如poly(GP))与大脑组织中的核心病理改变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脱节。一个看似“漂亮”的生物标志物数据,并不总能转化为真实的临床获益。未来的临床试验,必须更加谨慎地解读这些间接指标,并努力寻找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组织病理变化的标志物。
第二,鞘内给药并非“万无一失”的免疫避风港。研究首次在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系统地描绘了ASO药物可以引发持续的、可被监测的免疫应答(以CCL26为代表)。这场“免疫风暴”的利弊尚不明确,但它提醒我们,任何进入大脑的疗法,都必须将其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作为一个关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量因素。
第三,抵达不等于治愈。BIIB078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于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病理蛋白的累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患者出现症状时,神经元内可能已经“积重难返”。仅仅通过ASO阻断新的有毒蛋白合成,可能不足以清除存量巨大的“病理遗产”。未来的疗法,可能需要多管齐下,比如将ASO疗法与能够促进蛋白清除(如增强自噬或溶酶体功能)的策略相结合。
第四,细胞对药物的反应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RNase T2的案例,生动地展示了细胞面对外源治疗分子时所采取的主动适应甚至对抗策略。未来的药物设计,需要从“单向打击”的思维,转向考虑与细胞系统进行“双向互动”的更全面视角。
科学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它总是在不断的试错和反思中曲折前行。BIIB078的探索虽然未能抵达胜利的彼岸,但它在沿途留下的详细航海日志,无疑为后来者照亮了前路,让未来的航行能够避开暗礁,更精准地驶向治愈“渐冻症”及其他神经系统顽疾的终点。那些为这项研究献出生命的患者,他们的奉献将以这种方式,永远地镌刻在人类与疾病斗争的里程碑上。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