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Methods:从“平面战争”到“立体战场”!体外肿瘤模型的百年进化史
来源:生物探索 2025-08-01 17:35
从二维到三维,再到超越三维,体外肿瘤模型的演进之路,不仅是一部技术迭代的历史,更是一场深刻的科学思想变革。
在与癌症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人类智慧的前沿阵地之一,便是在实验室里构建能够模拟真实肿瘤的体外模型。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细胞培养,更是一场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乃至超越三维的认知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肿瘤生物学的理解,并为开发新的治疗策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7月25日,《Nature Methods》上发表的一篇题为“From 2D to 3D and beyond: the evolution and impact of in vitro tumor models in cancer research”的重磅综述,系统地描绘了这场革命的宏伟画卷。它引领我们穿越百年,从培养皿中的单层细胞,到能够“自我组织”的迷你器官,再到集成了微流控与人工智能的“芯片上的肿瘤”,见证我们是如何一步步在实验室里建造出一座座复杂的“肿瘤城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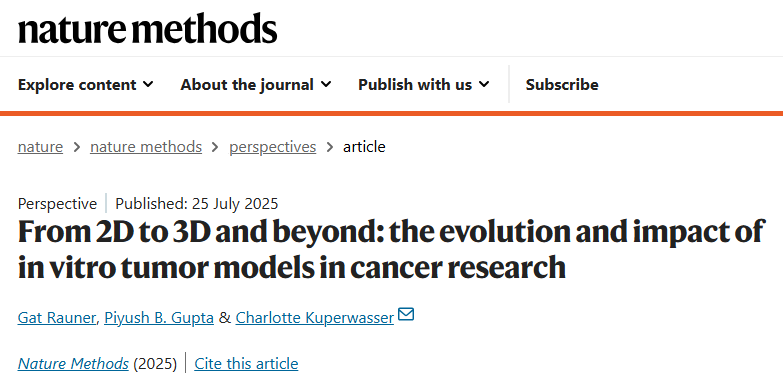
一张“地图”的诞生与局限
要理解这场模型革命的深刻意义,我们要先回到起点。故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那时,研究人员亚历克西斯·卡雷尔 (Alexis Carrel) 和蒙特罗斯·伯罗斯 (Montrose Burrows) 首次成功地让组织和细胞在体外环境中存活。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创举,但这些初代培养的细胞如同离水的鱼,生命短暂,很快就会衰老凋亡,这使得长期、系统的研究几乎无法进行。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51年。这一年,一个名为海拉 (HeLa) 的细胞系被成功建立。它源自一位名叫海莉耶塔·拉克斯 (Henrietta Lacks) 的宫颈癌患者,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永生”的细胞系。海拉细胞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无限增殖,为癌症研究提供了一个稳定、可再生的工具。它的出现,如同为癌症研究绘制了第一张可供反复查阅的“地图”,研究人员终于可以在分子、细胞和遗传层面上,对癌症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探索。
海拉细胞的成功,开启了一个细胞系开发的“黄金时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更多标志性的肿瘤细胞系,如乳腺癌细胞系MCF-7和MDA-MB-231等,相继问世。这些在塑料培养皿底部平铺生长的二维 (2D) 细胞,构成了一个扁平的“细胞社会”。它们整齐划一,易于观察和操作,成为了癌症研究的“标准模型”。
在这个“平面世界”里,研究人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识别并定性了癌基因 (oncogenes) 和肿瘤抑制基因 (tumor suppressor genes) 的关键作用,揭示了端粒酶 (telomerase) 在细胞永生化中的角色,并剖析了细胞衰老 (senescence)、凋亡 (apoptosis) 和自噬 (autophagy) 等核心生命过程。可以说,我们关于癌症大部分基础的分子和遗传机制的知识,都源自于对这些二维培养细胞的研究。它们就像一张张详尽的城市地图,标明了每一条街道和建筑,让我们对肿瘤细胞内部的信号通路和遗传事件了如指掌。
然而,这张“地图”终究是平面的。真实的肿瘤,远非这样一层平铺的细胞所能概括。人体内的肿瘤是一座喧嚣、混乱而又充满活力的三维“城市”。它不仅仅包含癌细胞,还有支持其生长的基质细胞 (stromal cells)、参与免疫反应的免疫细胞 (immune cells),以及将它们粘合在一起的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这座“城市”里,氧气和营养的供应是不均衡的,有些区域富饶,有些区域贫瘠,由此产生的梯度深刻影响着癌细胞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细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作用,这种三维结构和微环境的复杂性,恰恰是二维模型最致命的缺陷。
在二维培养皿中,所有细胞都均匀地暴露在培养基中,享受着同等的营养和氧气,这与真实肿瘤内部的微环境梯度天差地别。它们失去了三维空间中的邻里关系和结构支撑,细胞间的通讯方式也变得极其简化。这种过于简化的模型,就像一张只有街道名称却没有地形、建筑和居民的地图,它无法告诉我们这座“城市”是如何运作的,居民之间是如何交流的,又是如何应对外来威胁(如药物治疗)的。因此,基于二维模型筛选出的抗癌药物,在进入临床试验后往往遭遇惨痛的失败,因为它们攻击的,只是一个过于简化的“虚拟敌人”。研究人员意识到,要想真正理解并战胜癌症,就必须从“平面战争”走向“立体战场”,建造一个能真正模拟肿瘤复杂性的三维模型。
从平面到球体,迈向“立体”的第一步
意识到二维模型的局限性后,研究人员开始了向三维 (3D) 的探索。最早的尝试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被称为“球状体”(Spheroids) 的模型应运而生。它的构建方式非常巧妙:将癌细胞接种在不具粘附性的培养皿中,例如超低吸附板或悬滴培养 (hanging drop)。由于无法贴附在皿底,细胞们会自然地相互聚集,形成一个三维的细胞聚合体——球状体。
与平铺的单层细胞相比,球状体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首次在体外模拟了实体瘤的某些关键建筑特征。在一个足够大的球状体内部,外层的细胞可以充分接触营养和氧气,而核心区域的细胞则会因为供应不足而处于缺氧和低营养状态,甚至坏死。这种从外到内的梯度,真实地复现了实体瘤中常见的微环境梯度,为研究肿瘤生长、血管生成前的状态以及对放疗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平台。
在球状体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一种特殊的亚型——“肿瘤球”(Tumorspheres)。它通常由具有干细胞特性的癌细胞在无血清的特定培养基中形成。这些肿瘤球富集了癌症干细胞 (cancer stem cells),这类细胞被认为是肿瘤复发、转移和耐药的“万恶之源”。因此,肿瘤球模型在研究癌症干细胞生物学、肿瘤异质性、耐药机制和转移潜能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无论是球状体还是肿瘤球,它们都还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在最初的模型中,细胞仅仅是靠自身的力量聚合在一起。但在真实的人体组织中,细胞是“生活”在一个由蛋白质和多糖构成的复杂网络——ECM之中的。长期以来,ECM被认为仅仅是提供结构支撑的“脚手架”。直到1982年,研究人员米娜·比塞尔 (Mina Bissell) 和她的同事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ECM远非一个被动的支架,它是一个充满生物活性的信号中心,通过调节组织结构来深刻地影响着基因的表达和细胞的行为。
这个观点的提出,是癌症研究领域的一次思想地震。它意味着,细胞的“命运”不仅由其内在的基因决定,更受到其所处“社区环境”的深刻影响。ECM这个复杂的信号网络,能够指导细胞的分化、增殖甚至肿瘤的进展。
这一理论的实验验证,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一项关键的技术突破——基质胶 (Matrigel) 的诞生。基质胶是一种从小鼠肉瘤中提取的、富含层粘连蛋白 (laminin)、IV型胶原蛋白 (collagen IV) 等ECM成分的凝胶状蛋白质混合物。它在低温时是液体,在37°C时则会凝固成胶状,能够模拟体内基底膜的结构和功能。
基质胶的出现,彻底改变了3D细胞培养的面貌。它为细胞提供了一个更接近生理状态的3D环境,让研究人员能够观察细胞在更真实环境中的行为。到了20世纪末,许多里程碑式的研究都利用永生化的癌细胞系和基质胶,展示了3D培养系统在模拟发育和癌症中的巨大威力。更令人震惊的是,研究发现,通过改变基质胶环境,甚至可以将恶性的肿瘤细胞“诱导”回一个更正常的表型。这暗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可能性:或许我们不需要彻底杀死癌细胞,只要改造它们所处的“社区环境”,就能驯服它们,从而开辟全新的治疗策略。从二维到三维,从简单的细胞聚合体到嵌入基质胶的复杂结构,研究人员向着建造真实“肿瘤城市”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迷你器官的诞生,个性化“肿瘤城市”的崛起
进入21世纪,随着干细胞生物学的飞速发展,一种更高级、更仿生的3D模型横空出世,它就是“类器官”(Organoids)。类器官是由干细胞或祖细胞在体外特定条件下自我组织、分化形成的,能够再现来源器官的特定结构和功能的三维细胞培养物。它们就像在培养皿中长出的“迷你器官”。
最初的类器官主要源自健康的成体干细胞,例如从肠道、肝脏或乳腺组织中分离的干细胞。这些正常的类器官为了解组织稳态、再生和疾病建模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它们可以形成具有多细胞类型的复杂结构,但要模拟癌症,通常需要通过基因工程手段引入特定的突变。
真正的革命性突破,是“患者来源的类器官”(Patient-Derived Organoids, PDOs) 的创建。顾名思义,PDOs直接来源于患者的肿瘤组织,这些组织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活检甚至细针穿刺获得。这意味着,我们第一次能够在实验室里,为每一位患者建立一个“活的”肿瘤模型,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迷你肿瘤”。
PDOs的构建过程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首先,从患者身上获取的新鲜肿瘤组织需要经过精细的机械破碎和酶消化,将其分解成单个细胞或小的细胞团。这个过程需要拿捏得当,因为有些肿瘤的细胞间相互作用至关重要,过度消化会破坏这种连接;而另一些则需要彻底打散才能成功培养。接着,这些细胞悬液与基质胶混合,然后以“圆顶”(dome) 的形式小心地点在培养皿中央,或者均匀铺在孔底。基质胶在37°C下凝固后,为细胞的自我组织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支持和生化信号。最后,加入为特定肿瘤类型量身定制的培养基,其中包含关键的生长因子和小分子化合物,如Wnt通路激活剂、表皮生长因子 (EGF) 等,以促进细胞增起和分化。
在接下来的7到14天里,奇迹发生了。这些来自患者的癌细胞会在基质胶中重新组织,增殖并形成具有复杂三维结构的肿瘤样类器官。与之前使用永生化细胞系的模型相比,PDOs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们完整地保留了原始肿瘤的遗传突变、基因表达谱和细胞异质性。一座座形态各异、高度个性化的“肿瘤城市”就这样在实验室里拔地而起。
PDOs的建立成功率因肿瘤类型而异,总体在20%到80%以上。例如,乳腺癌PDOs的成功率可以超过80%,胰腺癌和结直肠癌也高达70%以上。而对于一些异质性更高、增殖缓慢或需要更特殊微环境的肿瘤,如前列腺癌,成功率则可能低于20%。
更进一步,研究人员还开发了“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类器官”(Patient-Derived Xenograft Organoids, PDxOs)。该技术先将患者的肿瘤组织植入免疫缺陷小鼠体内,让其在更接近生理的体内环境中生长。然后,再从这些小鼠身上取下增殖后的肿瘤,用于建立类器官。这个过程虽然更复杂,但为研究肿瘤在体内的演进和药物反应提供了又一个强大的模型。
PDOs最令人兴奋的应用在于个性化精准医疗。由于PDOs能高度模拟患者的真实情况,它们成为了理想的“药物试替身”。研究人员可以在这些“迷你肿瘤”上测试各种化疗药物或靶向药物的疗效,从而预测患者对特定治疗方案的反应,为临床医生制定最佳治疗策略提供宝贵的参考。这使得“对症下药”从一个概念,变为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同时,PDOs也可以被冷冻保存和复苏,这意味着可以为患者建立一个“活的”生物样本库,以备未来的研究和治疗探索之需。
超越“孤城”,构建动态的“肿瘤生态系统”
尽管PDOs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们仍非完美。当前的类器官模型,就像一座座孤立的“城市”,虽然内部结构复杂,却缺少了与外界的联系。它们通常缺乏关键的免疫细胞和基质细胞,也没有模拟血液流动的血管网络。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复杂的肿瘤微环境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这个微环境在肿瘤的生长、侵袭和对治疗的反应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对基质胶的依赖也带来了批次间不稳定的问题,限制了实验的可重复性。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研究人员开始探索更前沿的技术,力图将静态的“肿瘤城市”升级为动态的“肿瘤生态系统”。
1. 微型化与自动化:微类器官球 (MOSs) 与高通量筛选
为了解决传统PDOs培养耗时长、样本需求量大的问题,一种名为“微类器官球”(Micro-organospheres, MOSs) 的技术应运而生。它利用液滴微流控技术,可以从极小的活检样本中快速生成数千个均一的微型肿瘤球。这项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培养效率和可扩展性,使其更适合用于大规模的药物筛选,而且据报道,MOSs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始肿瘤中的基质和免疫细胞组分,为免疫治疗的测试提供了可能。初步研究显示,在转移性结直肠癌中,MOSs可以在14天内预测患者的药物反应,展现了其在精准肿瘤学中的巨大潜力。
2. 引入“血流”:芯片上的肿瘤 (Tumor-on-a-chip)
为了模拟肿瘤与血液循环系统的动态交互,研究人员将类器官技术与微流控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了“芯片上的肿瘤”(Tumor-on-a-chip)。这种模型在一个小小的芯片上集成了微通道网络,可以灌注培养基或“人造血液”,模拟体内的血流。肿瘤类器官、球状体或肿瘤组织切片被放置在芯片的特定腔室中,从而能够体验到流体剪切力、间质流等在静态培养中完全缺失的物理信号。
芯片上的肿瘤技术为研究肿瘤的动态过程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研究人员可以在芯片上建立血管网络,观察循环肿瘤细胞如何“逃离”原发灶,并顺着“血管”迁移到远端,模拟肿瘤转移的关键步骤。这种“芯片上的转移模型”(Metastasis-on-a-chip) 为测试抗转移药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此外,通过在芯片上整合不同的“器官模块”(如肝脏模块),还可以模拟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毒性反应,构建出“多器官芯片”(Multi-organ chip)系统。
3. “招募居民”:共培养系统与微环境重塑
为了让“肿瘤城市”不再孤单,研究人员正积极地为其“招募”新的居民。通过将肿瘤类器官与从患者体内分离的基质细胞(如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 CAFs)和免疫细胞(如T细胞)进行共培养,可以更好地重现肿瘤微环境的复杂细胞生态。研究发现,当胰腺癌PDOs与基质细胞和免疫细胞共培养时,其增殖和侵袭能力显著增强,这揭示了微环境对肿瘤恶性行为的强大驱动力。
一种特别巧妙的技术是“气液界面”(Air-Liquid Interface, ALI) 培养。该技术将细胞培养在一个具有多孔膜的特殊小室 (transwell) 中,膜的下半部分浸泡在培养基里以获取营养,而上半部分则暴露在空气中。这种方式模拟了肺、肠道等器官的上皮组织所处的生理环境。最近,研究人员将ALI技术与PDOs结合,成功地在体外模型中保留了肿瘤原始的T细胞受体谱系,为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免疫疗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这些前沿技术,正推动着体外模型从一个静态的、简化的细胞集合体,向一个动态的、多组分的、功能整合的“微型生态系统”演进。我们离在实验室里真正复现一个活生生的、功能完备的肿瘤,又近了一步。
挣脱“基质”的束缚,用智慧之眼洞悉未来
在构建更逼真的“肿瘤生态系统”的征途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基质胶 (Matrigel)。尽管它功勋卓著,但其源自小鼠肉瘤的“出身”带来了无法回避的问题:成分不明确、批次间差异大。这种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更重要的是,基质胶主要由层粘连蛋白和IV型胶原蛋白构成,其结构是球状的,这与人体大多数组织中由I型和III型胶原蛋白形成的纤维网状结构大相径庭。这种结构差异限制了细胞的正常行为,尤其是在细胞需要伸出伪足进行迁移和侵袭时。
为了挣脱基质胶的束缚,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材料科学,开启了一场对细胞外基质 (ECM) 的深刻重塑。
1. 从天然到合成:寻找更理想的“土壤”
一个重要的替代品是胶原蛋白 (Collagen),特别是I型胶原蛋白。它能形成纤维状的、具有一定刚性的网络结构,更真实地模拟了人体结缔组织的力学环境,为细胞提供了更生理化的“土壤”。研究表明,在胶原蛋白基质中,类器官能够更好地伸展和形成网络,展现出更复杂的组织形态。
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是合成水凝胶 (Synthetic hydrogels),例如聚乙二醇 (PEG) 水凝胶。合成水凝胶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可定制性”。研究人员可以精确地控制其物理和化学性质:例如,通过改变交联密度来调节硬度,以模拟大脑的柔软或软骨的坚硬,从而研究力学信号如何影响癌细胞;或者在水凝胶上偶联特定的生物活性分子(如RGD肽段)进行功能化修饰,精确控制细胞与基质的相互作用;甚至可以利用光敏水凝胶等“智能”材料,实现对微环境的动态调控,这是传统基质无法企及的。
这些新型基质材料的开发,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替代品,更是为了推动一种全新的建模理念——从“自我组装”(self-assembly) 到“引导性器官发生”(organogenesis-based formation)。传统的类器官依赖于干细胞的内在程序在基质胶中自发形成组织。而利用这些精心设计的工程化基质,研究人员可以主动地“引导”细胞,模拟从更原始的发育阶段到成熟组织的完整过程。这对于研究癌症是如何在组织发育的早期阶段萌芽,以及如何从癌前病变演变为恶性肿瘤,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 结合“智慧之眼”:先进成像与人工智能
拥有了更逼真的模型,我们还需要一双能够洞悉其内部奥秘的“眼睛”。高分辨率的活细胞动态成像技术,特别是共聚焦显微镜,让研究人员能够实时、三维地观察类器官内部的动态过程。他们可以连续数周追踪单个细胞的迁移、分化和增殖,亲眼目睹一个“肿瘤城市”的建立、扩张和对药物的反应。
然而,这些动态成像实验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仅靠人力分析如同大海捞针。此时,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学习成为了我们强大的“智慧之眼”。像QuPath和TrackMate这样的软件,已经能够利用算法自动进行图像分割与追踪,量化细胞的动态行为。而更先进的深度学习模型,虽然在3D生物图像分析中的应用尚在起步,但其潜力是巨大的。理论上,我们可以用海量的类器官图像或视频来训练AI模型,让它学会自动识别不同的细胞亚群、评估肿瘤形态变化、量化侵袭能力,甚至预测药物反应。
通过将最先进的体外模型与最前沿的成像及分析技术相结合,我们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我们不仅能“建造”一座肿瘤城市,还能成为这座城市的“全知观察者”,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和深度,洞察其运行的每一个细节。
模块化思维与癌症研究的新蓝图
从二维到三维,再到超越三维,体外肿瘤模型的演进之路,不仅是一部技术迭代的历史,更是一场深刻的科学思想变革。它反映了我们对癌症的理解,从一个以基因为中心的、还原论的视角,转向一个将肿瘤视为复杂生态系统的、整体论的视角。
未来的癌症研究蓝图,将由这些日益精密的模型共同绘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旧的模型就将被完全淘汰。恰恰相反,这场革命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模块化”的本质。二维细胞培养,因其简单、经济、高通量,在进行大规模初步筛选或研究特定细胞内信号通路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球状体模型,是研究实体瘤梯度和基本3D相互作用的绝佳工具。而复杂的、集成了多重元素的类器官和芯片上肿瘤系统,则为回答更深层次的、关于肿瘤微环境、药物反应和转移机制等系统性问题提供了终极平台。
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科学问题,像搭积木一样,选择和组合不同的模型模块。需要研究细胞内在的基因突变?一个简单的PDOs模型就足够了。想测试一种免疫疗法?那就需要一个包含免疫细胞的共培养系统。希望模拟药物在全身的代谢和毒性?一个多器官芯片将是最佳选择。
这种模块化的工具箱,赋予了癌症研究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力量。它使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探索癌症生物学的各个方面,从基质力学到免疫逃逸,从肿瘤异质性到细胞间的动态通讯。
我们正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开端。通过在实验室里建造出越来越逼真的“肿瘤城市”,并用最智慧的眼睛去观察它,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揭开癌症的神秘面纱。这条从平面到立体的演进之路,不仅将继续深化我们对生命奥秘的理解,更将为无数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引领我们最终走向一个能够真正预测、控制并战胜癌症的未来。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