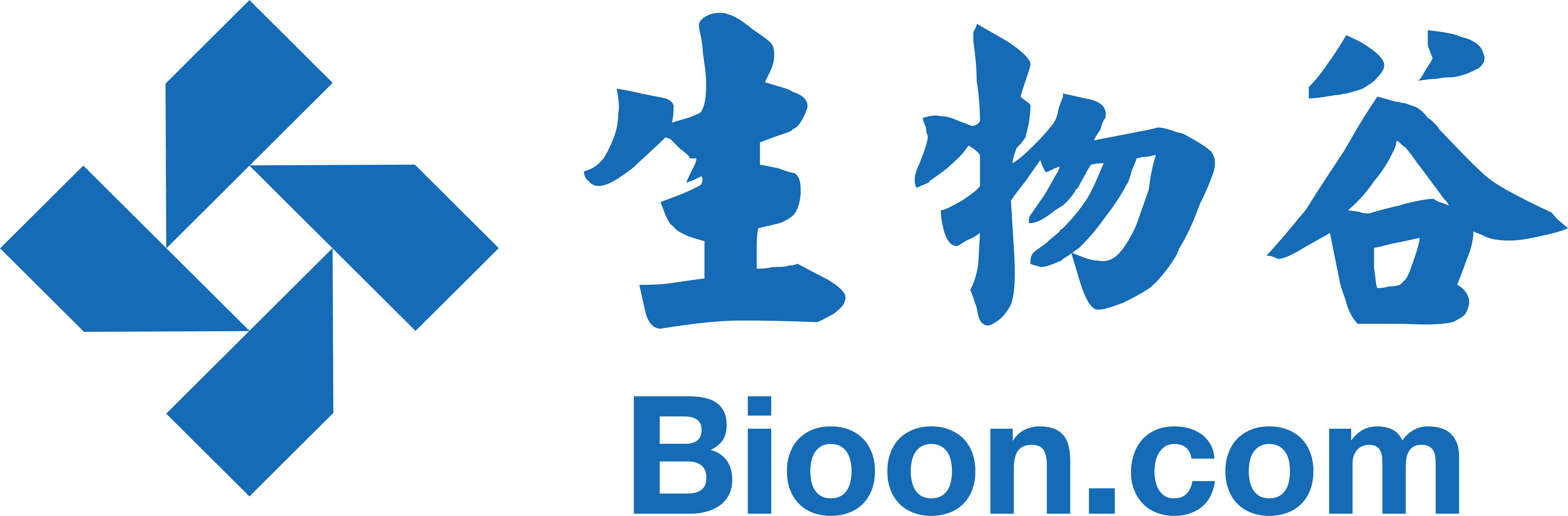从留学“窥”见中国医疗发展,三位“特殊”的留学生这样说......
来源:生物谷 2021-12-01 12:07
在医疗行业有很多像礼来这样的跨国药企来到中国,旨在于将全球肿瘤全领域甚至非肿瘤领域的创新药物尽快地带入中国,实现创新药物的”零“时差,助力国内的医疗领域发展,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而努力。
一位是曾经的联合国工作者,两位是如今的乳腺外科医生,一个相同点——留学。近日,善于跨界的外科医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杨犇龙教授与这三位“特殊”的留学生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一次留学生间的对话,也是一场关于中外医学诊疗模式与思维的“碰撞”。
这三位分别是:
范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进修;
陈阔: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主治医师,曾公派留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谢切诺夫第一医科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博士;
李晓于: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曾就职于联合国纽约总部,现就职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范蕾:我在哈佛的关键词是思考&无限
陈阔在俄罗斯生活了12年,最大的感受确实像国内所说的一样,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战斗民族”,但并不是真正地战斗,而是一种真性情的流露。从生活习惯来看,俄罗斯民族更是彰显出了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性格。
虽然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但是学医的留学生比例整体降低,并且由于“严进严出”的制度,医学生的毕业率也偏低。谈到俄罗斯医学体系,陈阔介绍道:”俄罗斯是沿用前苏联的体系,从细节上来讲是非常注重实践的。一次在妇产科课堂上,老师提出让我们‘体验’一下,就在上课中途领着学生进入产房,正巧碰到正在分娩的产妇,于是‘围观’产妇分娩直至下课。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上传染病课时,老师在带领学生进入病房前未告知患者的具体疾病,直到进入了病房,询问了流行病学史后才告诉我们是甲类传染病——霍乱。”
谈到在俄罗斯的从医经历,陈阔做住院医生时,每周都会联合各个科室对疑难病例进行多学科会诊(MDT)、每天对当天的手术进行总结、晨会上展示手术案例等。“从医学角度上看,俄罗斯医疗还是比较严谨和规范的。”陈阔说道。
陈阔的俄罗斯导师是著名的肿瘤学家,近期荣获了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陈阔谈道:“我和我导师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外国留学生。在我导师带着我出席许多学术会议的同时,我也促进了导师与中国各大医院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合作和交流。因此,我相信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实是合作共赢的一种状态——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也希望在疫情结束以后,中俄之间的学术以及临床实践交流能够更好地开展起来。”
谈到师生关系,杨犇龙也有感而发,“导师给我们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不管是刚刚从医还是逐渐成为成熟医生的过程,导师都会以不同方式在背后支持着自己的学生。就像外科医生最初可能是旁观导师做手术,逐渐成长到做导师的助手,最后则是做主刀医生,而导师在旁默默帮助。”他说。
随着中国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甚至能够”追平“国际水准,越来越多在外的华人会选择回国就医。陈阔谈到:”当俄罗斯华人、华侨咨询我们留学生是在俄罗斯治疗还是回国治疗时,我们普遍会推荐回国治疗。由于俄罗斯医疗体系的不同,且没有本地医保,海外治疗肿瘤的费用对比国内还是比较高的。并且这部分华人、华侨也相信中国的医疗水平,随着中国的不断繁荣强盛,越来越多在外的华人都会选择回国接受规范化地肿瘤治疗。“
李晓于:我在联合国的故事
大众普遍对联合国的理解都是”高大上“,李晓于对此表示:”确实有一部分工作是这样的,尤其是在纽约总部中的新闻部或者政治事务部,我曾经在《巴黎协定》签字仪式时接待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高丽先生。但联合国的工作不全是光鲜亮丽,我有很多同事会到军事冲突地区或者是难民区去接触当地最艰苦的工作。比如我师妹在也门工作期间,由于长期战乱,无法保证人身安全,晚上睡觉甚至要乘船至公海区域保证远离远程炮弹的袭击,这样的工作大概持续了两三年,真的非常辛苦。”
同时联合国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地方,从政治版图上联合国并不属于美国,而是属于193个成员国,即无“主””客”之分,这就使得联合国职员在不同意识形态下也会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而多元的另一面也是挑战性,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要充分地尊重别国的文化、宗教和政治。
谈到国内外就诊的差异,李晓于表示:“国内公立医院的医生每天面临的形形色色的病人很多,差异性也会很大,因此诊疗效率很高。而美国公立医院更像私人医院,对于患者的心理重视有时会too much,并且医疗费用非常高,以阑尾炎手术为例,在美国可能要花费达10万人民币。”
随着中国的医疗实力越来越强大,李晓于在联合国的工作中也会接触到中国专门派出的医疗队。“南苏丹的第三大城市瓦乌,有这样一支中国的医疗队,建在联合国区域大本营内,旁边就是难民营,他们经常去难民营义诊或接一些急诊。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医疗队有着丰富的应对恶劣环境下疑难杂症比如疟疾的经验,并且有对应的最先进、最前沿、最高效的治疗方案,能够快速的治愈这种高死亡率的疾病。包括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当中,我的外籍同事的家属在本国注射的都是中国的疫苗。”她说。
“留学”于个人而言是“行万里路”的自我丰富与提升,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合作交流也是很大的促进。各行业之间的跨国交流也是一种“留学”。在医疗行业有很多像礼来这样的跨国药企来到中国,旨在于将全球肿瘤全领域甚至非肿瘤领域的创新药物尽快地带入中国,实现创新药物的”零“时差,助力国内的医疗领域发展,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而努力。
这三位分别是:
范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麻省总医院进修;
陈阔: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主治医师,曾公派留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谢切诺夫第一医科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博士;
李晓于: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毕业,曾就职于联合国纽约总部,现就职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范蕾:我在哈佛的关键词是思考&无限
李晓于对哈佛大学的初印象给出了一个词——无限,范蕾对此也表示认同,“进入哈佛,首先要有无限的奋斗,在我认为‘无限’更多的体现在哈佛的整个环境当中,在哈佛,你可以有无限的想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范蕾在哈佛师从Paul E. Goss教授,是美国乳腺癌/内分泌研究领域的“大牛”,Paul E. Goss教授告诉范蕾在哈佛要做的第一件事是“thinking”。范蕾谈到:“Paul E. Goss教授让我有了无限的想法并将其付诸行动,也正是这样的想法驱动了我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乳腺癌进行研究,在《THE LANCET Oncology》上发表了《Breast cancer in China》。”
在中美医学教育方面也有所不同,美国的医学教育是以四年的通识教育为基础再进行医学专科教育,杨犇龙表示:“其实关于医学教育的改革,中国也一直在探索,我想最优的方法也肯定不是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而是发展中国特色模式。”同时范蕾提到:“美国是认同中国的医学教育的,五年制的本科教育在美国等同于大学,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则可以在美国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但难度还是较大。在美国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临床医生面临的晋升压力也是巨大的,并且会有淘汰制,同时晋升制度与中国的客观标准有所不同,美国晋升标准更倾向于‘peer review’即需要周围同事给予认可。”
范蕾学习工作所在的美国麻省总医院(MGH)癌症中心引领着很多新型药物的临床研究,甚至有望改变临床实践和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进程。“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距离得非常近,因此MIT的转化型实验室研发、筛选出新药后,很快就会在美国麻省总医院做Ⅰ期临床试验。因此,虽然美国麻省总医院的患者体量不如中国(比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但其承接的临床研究特别多,也会定期进行各种汇报,对能够参加临床研究的患者资源利用度是很高的。同时在临床试验的实施过程中,除了医院本身的团队以外还会有更加专业的管理机构来进行进一步地规范。整体上,美国麻省总医院是开放且合作的氛围。”范蕾谈到。对此,杨犇龙也深有体会,他说:“我和范蕾教授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化发展的模式,总体目的都是为了让创新药物尽快进入临床,从而惠及到更多的患者,这也是医学发展的目标。”
结束了在哈佛的学习后,范蕾放弃了在国外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国继续从医。在谈到自己的选择时,范蕾说:“在海外留学给予了我扩宽眼界和边界的机会——我学习到了很多关键且重点的肿瘤药物,回国后我也进行了药物研究的相关工作。此前,药物要进口到国内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譬如最早的一批靶向药物,可能需要8-10年,而造成这种长周期的原因则是国内外临床研究的不同步。
而现在,中国临床研究的水准也达到了国际水平,使得更多新药快速甚至同步落地中国临床实践,以乳腺癌内分泌药物阿贝西利为代表的创新药,国外临床数据出炉后,在中国同步递交对应适应证申请,从而使得可及性大大提高,中国患者能够更加迅速、便捷地从阿贝西利中获益。”
探索阿贝西利在激素受体阳性(HR+)/HER-2 -乳腺癌不同阶段治疗价值的MONARCH系列研究也于近日再次“开花结果”——在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人群辅助治疗中进行的monarchE研究结果显示:阿贝西利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复发风险,打破了同类研究无阳性结果的“魔咒”,成为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此类患者的CDK4/6抑制剂。《Cancer》曾发表的一篇有关CDK4/6抑制剂的综述化用了《指环王》中至尊魔戒上的刻字作为标题:One Monarch(君主) to rule them all,目前看来,似乎正是如此。
范蕾学习工作所在的美国麻省总医院(MGH)癌症中心引领着很多新型药物的临床研究,甚至有望改变临床实践和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进程。“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距离得非常近,因此MIT的转化型实验室研发、筛选出新药后,很快就会在美国麻省总医院做Ⅰ期临床试验。因此,虽然美国麻省总医院的患者体量不如中国(比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但其承接的临床研究特别多,也会定期进行各种汇报,对能够参加临床研究的患者资源利用度是很高的。同时在临床试验的实施过程中,除了医院本身的团队以外还会有更加专业的管理机构来进行进一步地规范。整体上,美国麻省总医院是开放且合作的氛围。”范蕾谈到。对此,杨犇龙也深有体会,他说:“我和范蕾教授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化发展的模式,总体目的都是为了让创新药物尽快进入临床,从而惠及到更多的患者,这也是医学发展的目标。”
结束了在哈佛的学习后,范蕾放弃了在国外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国继续从医。在谈到自己的选择时,范蕾说:“在海外留学给予了我扩宽眼界和边界的机会——我学习到了很多关键且重点的肿瘤药物,回国后我也进行了药物研究的相关工作。此前,药物要进口到国内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譬如最早的一批靶向药物,可能需要8-10年,而造成这种长周期的原因则是国内外临床研究的不同步。
而现在,中国临床研究的水准也达到了国际水平,使得更多新药快速甚至同步落地中国临床实践,以乳腺癌内分泌药物阿贝西利为代表的创新药,国外临床数据出炉后,在中国同步递交对应适应证申请,从而使得可及性大大提高,中国患者能够更加迅速、便捷地从阿贝西利中获益。”
探索阿贝西利在激素受体阳性(HR+)/HER-2 -乳腺癌不同阶段治疗价值的MONARCH系列研究也于近日再次“开花结果”——在高危早期乳腺癌患者人群辅助治疗中进行的monarchE研究结果显示:阿贝西利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复发风险,打破了同类研究无阳性结果的“魔咒”,成为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此类患者的CDK4/6抑制剂。《Cancer》曾发表的一篇有关CDK4/6抑制剂的综述化用了《指环王》中至尊魔戒上的刻字作为标题:One Monarch(君主) to rule them all,目前看来,似乎正是如此。
陈阔:我在“战斗民族”俄罗斯留学的日与夜
陈阔在俄罗斯生活了12年,最大的感受确实像国内所说的一样,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战斗民族”,但并不是真正地战斗,而是一种真性情的流露。从生活习惯来看,俄罗斯民族更是彰显出了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性格。
虽然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但是学医的留学生比例整体降低,并且由于“严进严出”的制度,医学生的毕业率也偏低。谈到俄罗斯医学体系,陈阔介绍道:”俄罗斯是沿用前苏联的体系,从细节上来讲是非常注重实践的。一次在妇产科课堂上,老师提出让我们‘体验’一下,就在上课中途领着学生进入产房,正巧碰到正在分娩的产妇,于是‘围观’产妇分娩直至下课。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上传染病课时,老师在带领学生进入病房前未告知患者的具体疾病,直到进入了病房,询问了流行病学史后才告诉我们是甲类传染病——霍乱。”
谈到在俄罗斯的从医经历,陈阔做住院医生时,每周都会联合各个科室对疑难病例进行多学科会诊(MDT)、每天对当天的手术进行总结、晨会上展示手术案例等。“从医学角度上看,俄罗斯医疗还是比较严谨和规范的。”陈阔说道。
陈阔的俄罗斯导师是著名的肿瘤学家,近期荣获了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陈阔谈道:“我和我导师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我是他第一个外国留学生。在我导师带着我出席许多学术会议的同时,我也促进了导师与中国各大医院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合作和交流。因此,我相信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实是合作共赢的一种状态——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也希望在疫情结束以后,中俄之间的学术以及临床实践交流能够更好地开展起来。”
谈到师生关系,杨犇龙也有感而发,“导师给我们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不管是刚刚从医还是逐渐成为成熟医生的过程,导师都会以不同方式在背后支持着自己的学生。就像外科医生最初可能是旁观导师做手术,逐渐成长到做导师的助手,最后则是做主刀医生,而导师在旁默默帮助。”他说。
随着中国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甚至能够”追平“国际水准,越来越多在外的华人会选择回国就医。陈阔谈到:”当俄罗斯华人、华侨咨询我们留学生是在俄罗斯治疗还是回国治疗时,我们普遍会推荐回国治疗。由于俄罗斯医疗体系的不同,且没有本地医保,海外治疗肿瘤的费用对比国内还是比较高的。并且这部分华人、华侨也相信中国的医疗水平,随着中国的不断繁荣强盛,越来越多在外的华人都会选择回国接受规范化地肿瘤治疗。“
李晓于:我在联合国的故事
大众普遍对联合国的理解都是”高大上“,李晓于对此表示:”确实有一部分工作是这样的,尤其是在纽约总部中的新闻部或者政治事务部,我曾经在《巴黎协定》签字仪式时接待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高丽先生。但联合国的工作不全是光鲜亮丽,我有很多同事会到军事冲突地区或者是难民区去接触当地最艰苦的工作。比如我师妹在也门工作期间,由于长期战乱,无法保证人身安全,晚上睡觉甚至要乘船至公海区域保证远离远程炮弹的袭击,这样的工作大概持续了两三年,真的非常辛苦。”
同时联合国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地方,从政治版图上联合国并不属于美国,而是属于193个成员国,即无“主””客”之分,这就使得联合国职员在不同意识形态下也会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而多元的另一面也是挑战性,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要充分地尊重别国的文化、宗教和政治。
谈到国内外就诊的差异,李晓于表示:“国内公立医院的医生每天面临的形形色色的病人很多,差异性也会很大,因此诊疗效率很高。而美国公立医院更像私人医院,对于患者的心理重视有时会too much,并且医疗费用非常高,以阑尾炎手术为例,在美国可能要花费达10万人民币。”
随着中国的医疗实力越来越强大,李晓于在联合国的工作中也会接触到中国专门派出的医疗队。“南苏丹的第三大城市瓦乌,有这样一支中国的医疗队,建在联合国区域大本营内,旁边就是难民营,他们经常去难民营义诊或接一些急诊。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医疗队有着丰富的应对恶劣环境下疑难杂症比如疟疾的经验,并且有对应的最先进、最前沿、最高效的治疗方案,能够快速的治愈这种高死亡率的疾病。包括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当中,我的外籍同事的家属在本国注射的都是中国的疫苗。”她说。
“留学”于个人而言是“行万里路”的自我丰富与提升,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合作交流也是很大的促进。各行业之间的跨国交流也是一种“留学”。在医疗行业有很多像礼来这样的跨国药企来到中国,旨在于将全球肿瘤全领域甚至非肿瘤领域的创新药物尽快地带入中国,实现创新药物的”零“时差,助力国内的医疗领域发展,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而努力。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87%用户都在用生物谷APP 随时阅读、评论、分享交流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