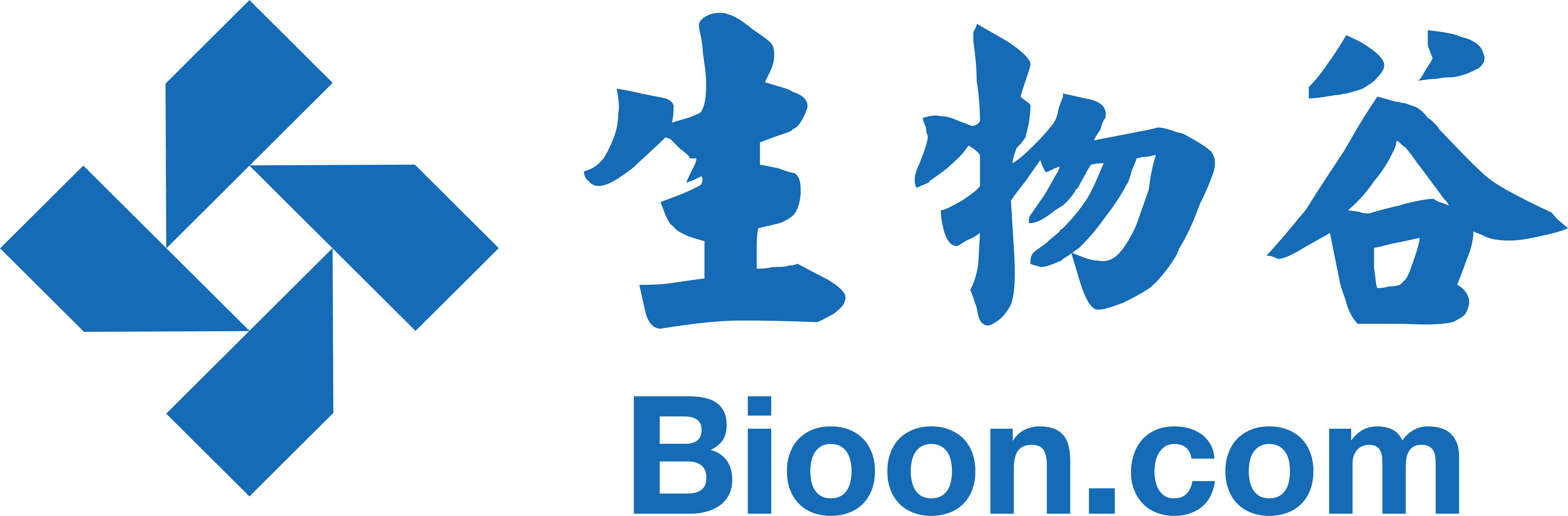Nature:告别“挨针”?鼻腔疫苗——呼吸道感染的终极防御新策略!
来源:生物世界 2025-05-14 10:51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鼻腔疫苗是安全的,能够预防病原体入侵,并在黏膜表面和全身性位点抑制严重疾病。
疫苗是我们对抗传染病的强大武器。从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现天花疫苗至今,疫苗家族不断壮大,拯救了无数生命。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更是让基于mRNA技术的注射型疫苗大放异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问世,并卓有成效地控制了由SARS-CoV-2引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
然而,当我们为注射疫苗的成就欢呼时,也逐渐认识到它的局限性。这些“明星”疫苗虽然能有效诱导全身性免疫(systemic immunity),产生大量能在血液中中和病毒的血清IgG抗体,但这更多是防止病毒进入体内深处造成严重损害。对于像新冠病毒、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这类主要通过呼吸道入侵的病原体,注射疫苗在它们入侵的“第一线战场”——呼吸道黏膜表面,防御能力却相对有限。这意味着,即使接种了注射疫苗,我们仍有可能被感染,并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那么,有没有一种疫苗,能够直接武装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在病原体敲门之前,就在门口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呢?这就是鼻腔疫苗(Nasal vaccines)!这项充满前景的策略,瞄准呼吸道感染的源头,旨在通过鼻内给药,不仅诱导全身免疫,更能激发强大的黏膜免疫(mucosal immunity),特别是分泌型IgA(secretory IgA, SIgA)。SIgA就像是驻守在呼吸道表面的“守卫”,能够直接阻断病原体入侵,从而有望从根本上减少感染,甚至阻止传播,同时减轻疾病严重程度。
开发鼻腔疫苗并非易事,它需要我们深入理解鼻腔复杂的解剖、生理和免疫特性,甚至要考虑鼻腔与中枢神经系统(CNS)的潜在关联。这不仅是免疫学的挑战,更是微生物学、生物材料学、生物工程学和化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前沿领域。5月7日《Nature》“Nasal vaccines for respiratory infections”。

第一道防线:身体的“空气过滤与预警系统”——呼吸道黏膜和NALT
要理解鼻腔疫苗为何重要,首先要认识我们的呼吸道黏膜(respiratory mucosa)以及隐藏其中的特殊免疫组织。想想看,我们每天呼吸空气,空气中充斥着各种微生物、灰尘和异物。呼吸道黏膜就像是身体的第一道“空气过滤系统”。
这层黏膜表面覆盖着纤毛上皮细胞(ciliated epithelial cells),这些细胞上的纤毛会不断摆动,将吸入的颗粒物向外推送,比如鼻腔中的纤毛会将东西推向咽喉,最终被吞咽或咳出。同时,黏膜上还有杯状细胞(goblet cells)分泌黏液(mucus),这些黏液能捕捉吸入的病原体和颗粒。纤毛的运动结合黏液的捕捉,构成了黏膜纤毛清除系统(mucociliary clearance),这是鼻腔物理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病原体进入身体。
然而,这层物理屏障并不是密不透风的。病原体总有机会突破。此时,黏膜下的免疫系统就需要发挥作用了。在鼻腔和咽喉区域,存在一种被称为鼻咽相关淋巴组织(nasopharyngeal-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NALT)的关键免疫组织。这就像是部署在“前线”的“军事基地”。
对于人类来说,NALT主要由不成对的鼻咽扁桃体(即腺样体)和成对的腭扁桃体(俗称扁桃体,它们共同构成了Waldeyer's环)组成。这些组织内部结构复杂,包含了启动和调节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所需的各种细胞,包括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s, APCs)如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和巨噬细胞,以及B细胞和T细胞。值得一提的是,人类的腺样体中观察到活跃的生发中心(germinal centre)形成,这是产生高亲和力抗体(包括IgA)的关键场所。
病原体或疫苗抗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被NALT捕获。NALT的黏膜上皮层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微褶细胞(microfold cells, M cells),它们能捕获腔道内的抗原,并迅速将其转运到下方的APCs。此外,位于鼻腔黏膜的呼吸道上皮层也含有呼吸道M细胞,它们提供了另一个抗原摄取位点。更有意思的是,黏膜下的树突状细胞可以将树突伸入鼻腔腔道,直接捕获鼻内给药的抗原。
被捕获的抗原随后被APCs处理,并将免疫原性肽段呈现在细胞表面,激活NALT内部的T细胞,包括辅助性T细胞(T helper cells, TH细胞,如TH1、TH2和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和B细胞。在TH细胞(特别是TH2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TGFβ1和IL-5)的诱导下,B细胞会发生IgA类别转换,分化成IgA+B细胞。
这些NALT来源的IgA+B细胞具有独特的“归巢”特性。它们表达特定的趋化因子受体,比如CCR10,使得它们能够迁移到表达相应配体CCL28的黏膜效应位点,如鼻甲和腺体组织。这种有针对性的迁移构成了“共同黏膜免疫系统”(common mucosal immune system)的概念基础——在一个黏膜部位(如鼻腔)诱导的免疫反应,可以在其他远端黏膜部位(如肺部、肠道甚至生殖道)产生保护作用。一项研究就通过过继转移淋巴B细胞,证明了共同黏膜免疫系统的存在,这些细胞可以迁移到远端和不同的黏膜组织。
迁移到鼻黏膜后,IgA+B细胞进一步分化为浆细胞(plasma cells),开始产生多聚体IgA(polymeric IgA)。多聚体IgA随后结合上皮细胞基底膜上的多聚体免疫球蛋白受体(polymeric immunoglobulin receptor, pIgR),形成复合物被转运穿过上皮细胞,最终以分泌型IgA(secretory IgA, SIgA)的形式释放到黏膜腔道中。
SIgA是黏膜免疫的“明星分子”。它拥有多个抗原结合位点,能够像“网”一样捕捉病原体,并阻止它们附着于黏膜表面,从而从源头阻断感染。新冠疫情期间的研究再次强调了SIgA的重要性。一项研究发现,感染SARS-CoV-2的个体,其病毒脱落持续时间与分泌型IgA抗体反应延迟有关,这表明SIgA在阻止病毒脱落和传播中的关键作用。另一项研究则通过工程化改造SARS-CoV-2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RBD)特异性的单克隆IgG抗体,使其转变为二聚体或分泌型IgA1抗体,结果发现工程化的二聚体和SIgA1抗体对包括Omicron BA.1、BA.2和BA.4/5在内的多种变异株表现出更高的中和活性。
因此,开发能够有效诱导局部抗原特异性SIgA的鼻腔疫苗,以阻断病原体的初始入侵,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策略。
除了NALT,鼻腔黏膜的呼吸道上皮层也提供了抗原采样途径。一项研究发现,鼻甲骨内衬的单层上皮细胞含有呼吸道M细胞,这为鼻内给药的抗原提供了替代性的摄取点。此外,树突状细胞也能通过伸展树突直接捕获鼻内给药的抗原,并将抗原转运至局部淋巴结(如颈淋巴结),启动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这些都使得鼻腔成为一个高效的抗原采样场所,有利于诱导黏膜抗原特异性免疫反应,使其成为疫苗递送的逻辑目标。
为什么注射疫苗不够?鼻腔疫苗的独特优势
对比注射疫苗和鼻腔疫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后者在应对呼吸道感染方面的独特优势。
首先,从使用者体验上,鼻腔疫苗具有显著的实用优势。它们通常通过喷雾或滴剂给药,避免了注射带来的疼痛和焦虑,尤其对于儿童和害怕针头的人群来说,这极大地提高了疫苗接种的依从性。其次,许多鼻腔疫苗可以进行自我给药,这对于大规模疫苗接种,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扩大覆盖范围,具有巨大潜力。想象一下,在流感季节或疫情爆发时,人们可以在家中便捷地进行疫苗接种。
更重要的是,从免疫学角度看,鼻腔疫苗提供了注射疫苗难以比拟的全面保护。注射疫苗主要诱导全身性免疫(例如血清IgG),能够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但往往难以在呼吸道黏膜表面产生足够的免疫反应。而鼻腔疫苗则不同,它不仅能诱导全身性免疫(产生血清IgG),更能有效启动局部黏膜免疫(产生分泌型IgA)。 SIgA像前文所述,能够直接在病原体入侵的“城墙”上布防,阻止它们进入身体。
此外,鼻腔疫苗还能诱导CD4+和CD8+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T resident memory, TRM cells)在呼吸道组织中形成。肺部的TRM细胞能够提供长期免疫力,并在小鼠模型中被证明可以保护动物免受致死性病毒感染。令人振奋的是,呼吸道CD8+ TRM细胞甚至在没有病毒特异性抗体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减少病毒的感染和传播。这就像是驻守在“城墙”内部的“特种部队”,一旦敌人突破防线,它们能迅速响应,限制病毒的扩散。
一项使用小鼠流感模型的研究就展示了鼻腔疫苗诱导交叉反应性免疫的潜力。研究发现,通过鼻腔而非全身免疫接种重组流感神经氨酸酶蛋白,可以诱导组织驻留的IgA产生细胞产生交叉反应性IgA抗体,从而提供针对异源和同源病毒感染的保护。这种交叉保护能力在病毒不断变异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真实世界的数据也支持鼻腔疫苗的有效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目前批准的唯一一款鼻内疫苗是FluMist四价减毒活流感疫苗。一项2003年的人体临床试验显示,FluMist在预防三种不同亚型流感病毒感染方面,提供了比注射型三价灭活疫苗更广泛的保护。尽管FluMist目前仅被批准用于2至49岁健康个体,且不适用于免疫功能低下或孕妇,但其便捷性(无需处方,可在医疗机构外接种)已被证明。另一款鼻内减毒活流感疫苗(AstraZeneca,2018/19配方)在人体研究中也显示,能在黏膜和血液中分别诱导IgA和IgG反应。该研究还发现,鼻内免疫接种后8小时内出现黏膜IL-33相关TH2型免疫反应,7天后出现差异化的CD8+ T细胞和循环TFH细胞反应,这些反应被认为是鼻腔疫苗诱导保护的潜在相关性指标。
总之,由于大多数呼吸道感染始于黏膜表面,能够同时诱导局部黏膜免疫和全身免疫的鼻腔疫苗,被认为是诱导针对感染的广泛保护的合理手段。
挑战与机遇:如何让疫苗顺利穿过“鼻腔迷宫”?
尽管前景光明,但开发成功的鼻腔疫苗并非易事。鼻腔独特的生理环境给疫苗递送带来了诸多挑战,就像是试图穿过一个充满障碍的“迷宫”。
首先,鼻腔分泌物会迅速稀释疫苗抗原。其次,黏膜纤毛清除系统会不断将抗原向后推送并清除,这极大地限制了抗原在鼻腔停留的时间,可能影响抗原与免疫细胞的结合和 uptake(摄取)。此外,鼻腔分泌物中含有蛋白酶和氨肽酶,可能会降解疫苗抗原。同时,人类鼻腔给药液体的体积非常有限,大约只有200微升,这要求疫苗制剂必须高度浓缩且有效。
这些物理和生理特性,都必须在鼻腔疫苗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为了克服这些挑战,研究人员整合了免疫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创造出了一系列新颖的递送系统(delivery systems),包括复制型和非复制型疫苗载体。
微小力量,巨大潜力:递送系统的创新
疫苗递送系统是鼻腔疫苗成功的关键之一。它们就像是“快递小哥”,负责将疫苗抗原安全、高效地送达免疫细胞所在的“目的地”。
复制型递送系统
复制型递送系统使用能够进行有限复制的病毒或细菌作为载体,比如重组腺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和疱疹病毒等。这些载体进入体内后会持续表达疫苗抗原,并在一定程度上模拟自然感染,从而诱导强烈的免疫反应,包括局部细胞毒性T细胞反应,且通常无需额外佐剂(adjuvant)。例如,一项在血清阴性健康成人中进行的I期临床试验显示,使用副流感病毒5型(PIV5)作为载体、编码RSV F蛋白的鼻腔疫苗(BLB201)是安全的,且免疫原性良好,诱导了鼻腔和血清RSV F特异性抗体反应以及抗原特异性CD4+和CD8+T细胞。
此外,一些细菌载体如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沙门氏菌(Salmonella)和李斯特菌(Listeria)也被用于研究。乳酸杆菌作为一种非致病且相对安全的载体,在针对鼠疫耶尔森氏菌、结核分枝杆菌和SARS-CoV-2的鼻腔疫苗研究中显示出潜力。
非复制型和生物相容性递送系统
为了解决复制型递送系统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如病毒回变、潜在的复制风险等),研究人员也开发了非复制型病毒载体以及基于生物材料和纳米材料的非复制型递送系统。
非复制型病毒载体通常是经过改造的病毒,虽然保留了感染细胞并表达抗原的能力,但不能在体内进行复制。腺病毒载体由于其固有的感染能力,可以快速表达疫苗抗原并刺激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被认为是一个有前景的疫苗平台。
基于生物材料和纳米材料的递送系统则更加多样化,它们通常由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聚合物或其他化合物构成,可以通过控制粒径、表面性质等特性来优化抗原递送。这些纳米材料可以携带抗原,并赋予其在鼻腔特殊环境中更强的稳定性和靶向性。
其中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系统是阳离子胆固醇化普鲁兰多糖纳米凝胶(cationic cholesteryl group pullulan nanogel, cCHP)。最初的CHP纳米凝胶是由普鲁兰多糖(一种葡萄糖基多糖)和胆固醇基团组成的,可以形成直径约40纳米的球形疏水聚集体。蛋白质抗原很容易被包裹在纳米材料内部,并以折叠的天然活性形式释放出来,这种独特的特性被称为“人工伴侣活性”(artificial chaperone activity)。为了增强其与带负电的鼻腔上皮的结合效率,研究人员在CHP纳米凝胶中引入了阳离子氨基,从而创建了cCHP。
cCHP纳米凝胶作为鼻腔疫苗递送系统显示出巨大潜力,目前已有多种针对呼吸道感染的cCHP基疫苗正在开发中。例如,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表面蛋白A(PspA)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疫苗抗原,因为它能诱导对不同血清型的交叉反应性免疫。针对所有肺炎链球菌血清型,研究人员开发了含有PspA的cCHP纳米凝胶(cCHP-PspA),并在小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中进行了测试。在小鼠中,鼻内接种cCHP-PspA不仅诱导了鼻腔灌洗液和血清中特异性的SIgA和IgG抗体,还显著减少了鼻腔和肺部细菌数量,提供了针对致命性肺炎链球菌呼吸道攻击的保护。cCHP-PspA鼻腔疫苗在恒河猴中的测试也显示,能诱导高滴度的PspA特异性血清IgG和黏膜IgA抗体,并提供针对不同血清型肺炎链球菌气管内攻击的保护。这些临床前研究证实了cCHP-PspA鼻腔疫苗作为未来人体临床试验候选者的潜力。
cCHP系统还被用于靶向非分型流感嗜血杆菌(nontypeable Haemophilus influenzae, NTHi),它是引起中耳炎、鼻窦炎和肺炎的常见病原体。由于P6蛋白在90%的NTHi菌株中保守,研究人员将其整合到cCHP纳米凝胶中(cCHP-P6)。小鼠研究显示,cCHP-P6能有效诱导鼻腔或中耳液中P6特异性IgA抗体,并抑制NTHi生物膜形成。这表明cCHP-P6纳米凝胶鼻腔疫苗有望预防NTHi引起的感染。
cCHP递送策略也被应用于呼吸道病毒感染,例如RSV。RSV是导致儿童和老年人呼吸道感染的主要原因。一项研究使用RSV小疏水蛋白(SHe)的胞外域作为抗原,并将其与载体蛋白PspA连接(SHe-PspA),再用cCHP纳米凝胶制备疫苗(cCHP-[SHe-PspA])。在小鼠和棉鼠(人类RSV感染的首选模型)中进行鼻内免疫接种,结果显示诱导了SHe特异性的黏膜IgA和血清IgG抗体。在棉鼠中,这些抗体有效控制了呼吸道黏膜和肺部的病毒感染。这项研究证明了cCHP也适用于亚单位鼻腔疫苗,可以对抗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一个显而易见的未来策略是开发二价cCHP-[SHe-PspA]鼻腔疫苗,同时诱导针对RSV和肺炎链球菌的免疫力。
除了cCHP,脂质体(Liposomes)也是一种有前景的生物相容性递送载体。脂质体是由磷脂和胆固醇组成的脂质双层形成的小囊泡,能够包裹抗原。其两亲性(amphiphilic)性质使其能够包封多种抗原。脂质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如脂质组成、结构和大小)可以根据疫苗抗原的特性进行调整,以最大化免疫原性。由于用于制备脂质体的磷脂来源于食物(如蛋黄和大豆),这种递送系统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除非对这些食物过敏。阳离子脂质体和经表面修饰(如粘膜粘附性聚合物)的脂质体被开发出来,以增强疫苗在鼻腔的粘附性和持久性。例如,使用钴卟啉-磷脂(CoPoP)脂质体鼻内递送重组流感血凝素三聚体,能有效诱导血凝素特异性免疫反应。CoPoP脂质体目前也正在进行COVID-19疫苗的临床试验。
壳聚糖(Chitosan)是另一种适用于黏膜递送的良好生物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和低毒性。壳聚糖还具有黏膜粘附性,并能松开上皮细胞紧密连接,从而促进抗原摄取。这种递送系统在小鼠鼻内免疫接种后,能诱导平衡的抗原特异性TH1和TH2介导的抗体反应。然而,壳聚糖的溶解性差是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潜在缺点,需要酸性条件下的溶解,随后可能发生水解。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壳聚糖的化学修饰(如增加亲水性、连接配体靶向特定细胞)以提高其适用性。基于壳聚糖的鼻腔疫苗候选者,使用白喉抗原和诺如病毒样颗粒,被证明是耐受性好且具有免疫原性的,能够诱导抗原特异性IgG和IgA反应。
SpyCage是一种能够自组装的60个亚单位的蛋白质支架,可以共价连接重组蛋白质抗原。一项概念验证研究显示,使用包被SARS-CoV-2刺突蛋白RBD的SpyCage,并与来自大肠杆菌热不稳定肠毒素的黏膜佐剂LTA1(一种缺乏颅神经毒性的变体)共同给药,在叙利亚仓鼠模型中显示出高免疫原性,并增强了鼻腔和肺部的病毒清除。
这些创新性的递送系统是克服鼻腔生理障碍、实现疫苗抗原有效递送的关键,也为开发安全有效的鼻腔疫苗奠定了基础。
后疫情时代的冲刺:新冠鼻腔疫苗正在路上
当前的肌肉注射型COVID-19疫苗在预防后续感染或限制传播方面效果有限,再次凸显了靶向呼吸道免疫系统的重要性。毕竟,SARS-CoV-2的感染始于呼吸道。开发第二代COVID-19疫苗,直接作用于呼吸道,显得尤为必要。
一项在血清阴性成人中进行的SARS-CoV-2鼻内疫苗人体挑战研究显示,与早期黏膜IgA和CD8+T细胞反应相关的免疫反应,与病毒载量控制密切相关。这进一步支持了鼻腔疫苗在减少感染和传播中的作用。
基于病毒载体的鼻腔疫苗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将禽副粘病毒3型(APMV3)载体表达SARS-CoV-2 S蛋白的疫苗鼻内单次给药仓鼠,诱导了针对原始毒株以及Alpha和Beta变异株的S特异性IgG和IgA抗体,并具有中和活性。这些仓鼠没有出现肺部炎症或呼吸道病毒复制。类似地,使用减毒副流感病毒3型(B/HPIV3)表达预融合稳定SARS-CoV-2 S蛋白的疫苗(B/HPIV3/S-6P)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诱导了S特异性气道黏膜IgA和IgG以及血清抗体,对Alpha、Beta和Delta变异株具有中和活性,但对Omicron亚系活性较低。攻击后,鼻内免疫的猕猴呼吸道和肺组织中检测不到病毒。另一项研究中使用活的、复制型嵌合B/HPIV3病毒载体表达预融合稳定S蛋白,鼻内单次免疫仓鼠,诱导了病毒特异性IgG和IgA,对SARS-CoV-2原始毒株、B.1.1.7和B.1.351变异株具有中和活性,攻击后仓鼠鼻腔和肺部检测不到病毒。
牛津大学/阿斯利康的腺病毒载体COVID-19疫苗ChAdOx1 nCoV-19(即Covishield),虽然是批准用于注射的疫苗,但随后的研究探索了其鼻内给药的效果。先前研究显示,肌肉注射ChAdOx1 nCoV-19/AZD1222能保护恒河猴免受肺炎,但不能减少上呼吸道病毒脱落。然而,后续对猕猴和仓鼠进行的鼻内免疫显示,攻击后呼吸道病毒检测量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ChAd鼻内疫苗不仅诱导广泛反应性IgG和IgA,还能诱导呼吸道中的病毒特异性记忆CD8+T细胞。一项在健康成人中进行的ChAdOx1 nCoV-19鼻内接种I期临床试验显示,作为单次加强接种,ChAdOx1 nCoV-19具有可接受的耐受性。然而,仅少数参与者观察到可检测的黏膜抗体,全身抗体反应微弱。这可能与用于该鼻腔疫苗的ChAdOx1载体来源于猿猴腺病毒血清型,对人呼吸道上皮细胞感染效率不高,导致SARS-CoV-2抗原表达水平较低有关。
为了进一步探讨腺病毒载体COVID-19鼻腔疫苗的适用性,一项独立研究比较了复制缺陷型腺病毒和单周期复制型腺病毒载体疫苗表达SARS-CoV-2 S蛋白的效果。结果显示,单周期复制型制剂产生的S特异性抗体水平更高。单次鼻内或肌肉注射单周期复制型腺病毒疫苗,均能降低SARS-CoV-2病毒载量和肺损伤。不过,重复接种载体基疫苗是否会导致抗载体免疫反应,从而降低未来病毒载体的感染效率和疫苗抗原递送,仍有待确定。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总体支持了病毒载体鼻腔疫苗用于抗SARS-CoV-2的可行性,显示出高免疫原性和保护性。然而,病毒载体鼻内递送在人体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另一项研究则进一步强调了鼻腔疫苗策略的重要性,开发了一种完全减毒的复制型SARS-CoV-2疫苗候选者SCPD9-AFCS作为鼻腔疫苗,并将其与注射型单价mRNA疫苗BNT162b2在预防SARS-CoV-2 B.1和Omicron BA.5变异株传播方面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SCPD9-AFCS在预防病毒传播方面优于注射型mRNA疫苗,进一步突出了鼻腔疫苗在这一方面的优势。
考虑到许多人已经接种了注射型mRNA疫苗,一种“首程注射,后续鼻喷”(prime-and-spike, P&S)策略被提出,即在现有注射诱导的全身性保护性免疫基础上,通过鼻内加强接种预融合稳定(Hexapro)的三聚体重组SARS-CoV-2 S蛋白,以激发黏膜免疫。在实验性啮齿动物中,P&S策略诱导了强大的黏膜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包括组织驻留记忆CD8+ T细胞以及IgA和IgG抗体。疫苗诱导的免疫力在接种后数月仍能保护小鼠免受病毒攻击,显示了疫苗的持久性。对免疫仓鼠的保护研究进一步证实了P&S策略的有效性,包括阻断病毒传播。一项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用二价Ad26基SARS-CoV-2疫苗候选者进行气管内加强接种的有效性,能够诱导黏膜体液免疫反应(具中和活性)和细胞免疫,为应对SARS-CoV-2 BQ.1.1攻击提供了接近完全的保护。这项研究提示,保护性疗效与黏膜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相关,并支持开发能够阻断呼吸道病毒入侵呼吸道黏膜的黏膜疫苗的可行性。
作为P&S策略广泛相关性和持久性的证据,一项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进行的异源XBB.1.16攻击研究,比较了鼻内接种WA1-BA.5二价猿猴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针,或注射WA1和BA.5或XBB.1.16 S蛋白二价mRNA加强针五个月后的保护效果。鼻内接种诱导了持久的气道IgG和IgA反应,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病毒复制极少。相比之下,注射mRNA疫苗仅限于下呼吸道的全身性B细胞介导保护。这项研究进一步支持了鼻腔疫苗在预防SARS-CoV-2感染方面的广泛有效性。
与鼻腔疫苗能够诱导强大黏膜免疫以预防SARS-CoV-2入侵和传播的预期一致,大量鼻腔疫苗候选者正在进行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疫苗追踪器的数据(截至2023年3月30日),有19种靶向呼吸道的疫苗候选者正在不同临床评估阶段,包括16种鼻内型、1种气溶胶型和2种吸入型。其中大多数是复制型或减毒病毒载体。例如,靶向SARS-CoV-2 S蛋白RBD的复制型流感病毒载体鼻腔疫苗,以及纽卡斯尔病病毒和腺病毒载体鼻腔疫苗(表达S蛋白)正在进行II/III期临床试验。非复制型载体疫苗包括PIV5基腺病毒载体疫苗(表达武汉原始株WA1的S蛋白),正在健康成人和年轻人中进行I期临床试验以评估安全性、反应原性和免疫原性。一款表达S蛋白的RSV载体减毒活疫苗MV-014-212也正在进行I期临床试验。此外,一款减毒活SARS-CoV-2鼻腔疫苗COVI-VAC也正在健康成人中进行临床研究。
除了病毒载体疫苗,基于重组蛋白(亚单位)的鼻腔疫苗也在积极开发中。一项近期研究显示,鼻内接种SARS-CoV-2 RBD亚单位疫苗与马司托拉肽-7(mastoparan-7,一种激活肥大细胞的寡肽)佐剂结合,能优先诱导多功能中央记忆T细胞(TCM cells)。鼻内诱导的TCM细胞反应具有T细胞固有特性,并在转移到幼稚宿主后得以维持,在肺部抗原攻击时促进增强的记忆召回。与同种抗原和佐剂的注射疫苗相比,鼻腔疫苗诱导的抗体对多种变异株具有广泛的中和活性。因此,鼻腔疫苗在仓鼠攻击模型中提供了临床疾病保护和更少的肺部组织病理学。这项研究为鼻腔疫苗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性证据,并强调了T细胞免疫在抗体反应之外的关键重要性。虽然疫苗领域历来关注体液免疫(抗体)作为保护性免疫的信息参数,但SARS-CoV-2感染的经验再次强调了T细胞介导免疫对于诱导针对病原体的记忆和保护性免疫的关键重要性。T细胞免疫已被证明即使在没有中和抗体的情况下也能控制病毒感染。显然,T细胞的贡献是疫苗开发中需要评估的重要反应。
许多国家也为COVID-19鼻内免疫做出了新贡献。古巴的CIGB-669,这是一款含有SARS-CoV-2 S蛋白RBD和乙肝病毒核衣壳抗原的重组蛋白亚单位候选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评估其单独鼻内给药或与肌肉注射联合给药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另一个正在评估的COVID-19亚单位鼻腔疫苗候选者是ACM-001,它包含包裹在CPG佐剂中的SARS-CoV-2 S蛋白,并封装在通过人工细胞膜技术形成的自组装纳米尺度囊泡中。
这些全球努力已取得初步成果,至少四个国家(中国、印度、伊朗和俄罗斯)已授予鼻腔疫苗紧急使用许可。中国批准了两种黏膜疫苗:一种是吸入型腺病毒载体疫苗(表达S蛋白),另一种是减毒活流感载体鼻腔喷雾疫苗(基于RBD)。印度批准了一款复制缺陷型猿猴腺病毒载体疫苗(编码预融合稳定S蛋白)作为成人鼻腔疫苗。伊朗批准了一款重组S蛋白基鼻腔疫苗,与水包油佐剂系统RAS-O结合,已被证明安全有效并能诱导保护性免疫。俄罗斯也据报道批准了一款异源重组腺病毒rAd26和rAd5联合疫苗的鼻腔使用。
面向未来的探索:鼻腔mRNA疫苗的可能性
鉴于mRNA疫苗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巨大成功,在未来的大流行准备中,黏膜递送mRNA疫苗是值得考虑的方向。然而,mRNA在鼻腔分泌物的酶作用下易降解,并且难以穿过黏膜屏障被清除,这为其鼻内递送带来了挑战。
创新的mRNA鼻腔递送系统正在开发中,旨在保护mRNA并促进其跨黏膜递送。一种基于阳离子聚乙烯亚胺-环糊精的鼻腔疫苗递送载体,通过其生物相容性,并能暂时打开紧密连接,促进mRNA跨鼻腔上皮递送。使用阳离子环糊精-聚乙烯亚胺2k偶联物与编码HIV gp120的阴离子mRNA复合,进行鼻腔mRNA疫苗接种的测试显示,诱导了强大的黏膜和全身性TH1、TH2和TH17免疫反应。类似策略也考虑了使用阳离子脂质体制剂进行鼻腔递送。
整合了生物工程、黏膜免疫学和疫苗学的专业知识,正在研发新的递送载体,用于靶向呼吸道病原体的鼻腔免疫,尽管mRNA在鼻腔恶劣环境中维持稳定性存在障碍。例如,一种可吸入的、可生物降解的聚胺-聚酯共聚物复合物已被研究用于递送编码SARS-CoV-2 S蛋白的mRNA到肺部。鼻内给药这些复合物,导致mRNA在肺部(包括上皮细胞和APCs)中高效转染,从而在小鼠中诱导了细胞和体液保护性免疫,对抗致命病毒攻击。另一项研究评估了鼻腔mRNA封装脂质纳米颗粒(mRNA-LNP)疫苗对抗SARS-CoV-2在叙利亚黄金仓鼠中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性疗效。鼻腔mRNA-LNP疫苗诱导了S特异性中和IgG和IgA抗体,降低了呼吸道病毒载量,减轻了肺部病理,并预防了SARS-CoV-2攻击后的体重减轻。总而言之,基于鼻腔mRNA疫苗在人类中诱导保护性免疫的潜力,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鼻腔疫苗的未来之路
正如该综述和其他研究所讨论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鼻腔疫苗是安全的,能够预防病原体入侵,并在黏膜表面和全身性位点抑制严重疾病。目前获批上市和临床使用的鼻腔疫苗数量有限。如前所述,FluMist四价减毒活流感疫苗是目前美国FDA批准的唯一一款用于2至49岁健康个体的鼻腔疫苗。然而,即使通过降低病毒毒力制造出减毒疫苗,对于免疫系统尚未成熟的婴儿或存在免疫衰老的老年人,减毒活疫苗的鼻内给药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因此通常不被批准使用。
鼻腔疫苗的安全性在其开发过程中必须得到充分考虑。例如,含有完整病原体的疫苗可能存在回变(reversion)风险。基于重组蛋白的亚单位疫苗似乎比活疫苗更安全,但纯化的重组蛋白(亚单位)抗原通常诱导的免疫反应较弱,通常需要与佐剂(免疫刺激剂)共同给药。目前注射疫苗中已使用多种佐剂(如铝盐、AS04、MF59、AS01B和CPG 1018),其他候选佐剂(如微生物衍生物、颗粒佐剂)也在临床试验中,这些候选佐剂可能被用于鼻腔亚单位疫苗制剂。
鼻腔疫苗开发的一个主要顾虑是鼻腔与中枢神经系统(CNS)的接近性。鼻腔上方的筛板紧邻嗅球(olfactory bulb),嗅球由连接大脑的特殊神经元组成。通过鼻腔给药的抗原,可能通过上皮细胞或邻近嗅球运输到大脑,从而对神经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小鼠和大鼠常用于疫苗开发,其鼻腔表面近50%被嗅觉上皮覆盖。相比之下,人类鼻腔内衬主要由呼吸道上皮覆盖(约90%),嗅觉上皮仅占剩余的10%。尽管人类嗅觉上皮面积相对较小,但其与CNS的接近性仍需在开发安全的鼻腔疫苗时加以考虑。此外,鼻腔疫苗不应影响支持嗅觉神经元的嗅觉上皮中的支持细胞(sustentacular cells),因为研究显示这些细胞在病原体感染期间会吸引髓系细胞,导致嗅觉上皮炎症并产生促炎细胞因子。
以一个历史风险为例,一种灭活鼻内流感疫苗与经过基因解毒的大肠杆菌热不稳定肠毒素突变体作为佐剂联合使用,曾被批准上市。然而,上市后监测发现该疫苗与面神经麻痹(Bell's palsy)病例相关,最终导致该疫苗停用。此外,含有AS03佐剂的灭活流感疫苗Pandemrix,在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中增加了患发作性睡病(narcolepsy)的风险。霍乱毒素结构与热不稳定肠毒素相似,曾作为黏膜佐剂进行实验性研究。在小鼠模型中,鼻内给药天然霍乱毒素可以通过嗅球运输到中枢神经系统,并在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神经损伤。因此,在开发鼻腔疫苗的同时,必须验证疫苗抗原和/或佐剂不会通过嗅觉上皮运输到中枢神经系统。候选鼻腔疫苗在启动临床试验前,必须仔细评估其所有成分的安全性,确保对中枢神经系统无不良影响。
总而言之,鼻腔疫苗开发需要考虑几个关键问题:
努力开发安全稳定的mRNA和亚单位疫苗制剂及递送系统;
基于感染前后的免疫组谱数据,明确对抗目标病原体所需的免疫类型(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组织驻留记忆和/或循环记忆,单独或组合);
创建最佳的鼻腔疫苗制剂和递送载体,以及适当佐剂的益处;
确保整体鼻腔疫苗的安全性。
尽管面临挑战,但鼻腔疫苗凭借其独特的优势——直接在前线构建免疫屏障,减少感染和传播,以及其便捷的给药方式——正日益成为应对呼吸道感染,特别是为未来大流行做准备的重要方向。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呼吸道感染防御,或许将不再仅仅依赖“挨针”,而更多地来自于我们鼻子里的这道希望之光。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