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Biotechnology:突破神经再生极限!数十万轴突穿越损伤区,H9-scNSC移植重建脊髓“神经接力”
来源:生物探索 2025-11-21 11:09
随着H9-scNSCs在GMP条件下的标准化生产成为可能,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技术能帮助那些被禁锢在轮椅上的灵魂,重新找回对身体的掌控。
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 SCI),一个在医学教科书上被长期标记为“不可逆”的残酷名词。全球范围内,约有700万人正生活在因脊髓损伤导致的瘫痪阴影中。对于这些患者而言,脊髓神经轴突的断裂不仅仅是运动功能的丧失,更意味着身体与大脑之间通讯的永久静默。
11月17日,《Nature Biotechnology》的研究报道“Extensive restoration of forelimb function in primate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by neur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研究人员利用临床级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功能性修复。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的胜利,更是对“神经无法再生”这一教条的有力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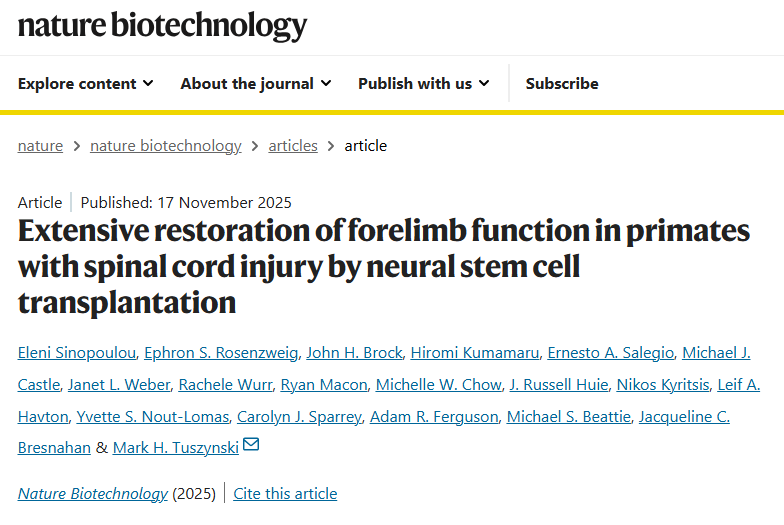
不仅仅是“填充”:构建跨越深渊的神经网络
在深入探讨这项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脊髓损伤修复的核心痛点。脊髓损伤后,受损部位会形成一个充满液体的空腔,周围伴随着胶质瘢痕(Glial Scar)。这就像是一座大桥被炸断,中间不仅那是万丈深渊,两岸还布满了阻止重建的“路障”。
过去的研究往往试图让受损的宿主轴突(Host Axons)直接跨越这个深渊,但这极其困难。而这项研究采取了一种更为巧妙的策略:“神经接力”(Neural Relay)。研究人员并没有奢望宿主的神经元能直接长过损伤区,而是希望植入的神经干细胞能在损伤中心分化为新的神经元,充当“中间人”。宿主的轴突只需长入移植物中,与新的神经元形成突触;然后,这些新的神经元再伸出轴突,长出移植物,连接到下游的宿主神经回路。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研究团队使用了名为 H9-scNSCs 的细胞系。(其中的“sc”后缀,它代表“脊髓”(Spinal Cord))。这并非普通的神经干细胞,而是经过特定转录因子(如HoxC家族)诱导,被赋予了“脊髓身份”的细胞。
研究数据显示,在损伤后两周(半切模型)或三至五周(挫伤模型)的亚急性期,研究人员将约 1000万至1400万 个这样的细胞移植到了受损区域。这不仅仅是细胞移植,研究人员还精心调制了一种包含纤维蛋白原、凝血酶以及多种生长因子(如BDNF、FGF2、VEGF)的基质,在微观尺度上进行了一次生态系统重建。
解剖学的奇迹:数十万轴突的“远征”
在接受移植的恒河猴脊髓中,人类神经干细胞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填满了原本空空如也的损伤空腔。组织学分析显示,移植物与宿主脊髓实现了无缝融合,且具备极高的血管化程度(Vascularization)。
最令人惊叹的数据来自于神经轴突的生长情况。在之前的研究中,再生轴突往往只有寥寥一两百根,且延伸距离不过1-2毫米。而在这项研究中,量变引起了质变。数据显示,从移植物中延伸出的轴突数量极其庞大。在损伤中心尾侧9毫米处测量,平均每只动物有 66,200 ± 25,100 根来自移植物的轴突。这一数字的范围甚至达到了26,700到139,900根!
更重要的是,这些轴突并非“短跑运动员”,而是“马拉松选手”。它们穿越了宿主的白质,延伸距离最长达到了 39毫米。这意味着,新生的神经纤维跨越了多个脊髓节段。在共聚焦显微镜下,研究人员清晰地观察到,这些带有绿色荧光蛋白(GFP)标记的移植物轴突,与下游的宿主神经元建立了真正的突触连接(Synapse Formation),完成了“接力”的最后一环。
从“能动”到“灵巧”:重新定义功能恢复
解剖结构是基础,但对于患者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是功能的恢复。研究人员使用了经典的“布林克曼板”(Brinkman Board)任务来评估手部精细运动功能。猴子需要用受损的手,通过拇指和食指的“捏取”(Pincer Grip)动作,将食物取出来。
在C7脊髓半切(Hemisection)模型中,结果对比鲜明。未接受移植的对照组猴子,其受损手部的功能恢复极差,平均成功率仅为 5.8% ± 5.4%。它们的手指往往呈现屈曲痉挛状态。
然而,接受了H9-scNSCs移植的猴子,表现出了惊人的恢复能力。它们不仅能够张开手掌,还能重新通过捏取动作获得食物。移植组的平均成功率达到了 53.4% ± 19.2%。
这是一个高达 9.2倍 的功能提升(P = 2.5 × 10⁻²⁷)。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完全失去手部功能的人来说,恢复53%的功能可能意味着他可以独立进食、操作轮椅,甚至敲击键盘。
挑战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挫伤模型的启示
为了让研究结果更接近临床转化,研究团队进一步挑战了更接近人类实际损伤情况的“挫伤”(Contusion)模型。在这个更为复杂的模型中,拥有存活移植物的猴子,其最终的功能恢复程度是对照组(移植物未存活的动物)的 2.9倍(P = 6.3 × 10⁻⁸)。
此外,通过磁共振成像(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在移植后3个月,T2加权成像上的信号变化可以准确预测移植物的存活情况。这种影像学与组织学的对应关系,为未来的临床试验提供了重要的监测手段。
被忽视的变量:康复训练与细胞治疗的“双人舞”
这项研究中最引人深思的发现之一,是“细胞”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在移植组中,康复训练参与度与功能恢复之间的决定系数(R²)高达 0.77(P = 0.059)。也就是说,越努力尝试使用受损手臂的猴子,其功能恢复得越好。
但在没有移植物的对照组中,这个规律完全失效了(R² = 0.07)。这一发现揭示了深刻的生物学逻辑:没有神经干细胞修复受损的神经回路(硬件),再多的康复训练也是徒劳;但仅有神经回路的修复是不够的,新生的神经连接需要通过不断的“使用”来强化。真正的治愈,来自于生物学治疗与行为学干预的完美结合。
细胞命运的精细调控:为何H9-scNSCs如此特殊?
定量分析显示,在移植物中,约 18% ± 6% 的细胞分化为神经元,51% ± 6% 分化为星形胶质细胞。这个比例非常接近正常人类脊髓灰质中的细胞组成。相比之下,该团队2018年的研究中,神经元比例高达57%。
H9-scNSCs这种更加“仿生”的分化比例,可能正是其功能优越性的细胞学基础。此外,在分化出的神经元中,71%表现为兴奋性神经元,15%为抑制性神经元,这种构成可能更有利于信号的传递和运动功能的驱动。
从实验室到病床:跨越“死亡之谷”的思考
尽管成果斐然,但从恒河猴到人类患者,仍面临挑战。首先是免疫抑制,未来临床可能需要采用类似治疗ALS试验中的一年期三联免疫抑制方案。其次是安全性,虽然本研究未观察到畸胎瘤(Teratoma),但长期安全性仍需监测。最后是时间窗口,研究选择在亚急性期(损伤后2-5周)进行移植,对于慢性期患者是否有效仍是未知数。
这项发表于《Nature Biotechnology》的研究依然是脊髓损伤治疗领域的一座灯塔。随着H9-scNSCs在GMP条件下的标准化生产成为可能,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技术能帮助那些被禁锢在轮椅上的灵魂,重新找回对身体的掌控。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