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里程碑式突破!I/IIa期临床试验证实hESC衍生细胞移植可安全并有效地重建帕金森病患者的多巴胺能系统
来源:生物探索 2025-10-16 09:31
研究详细报道了一项利用人胚胎干细胞衍生的多巴胺能祖细胞治疗帕金森病的I/IIa期临床试验结果。
我们大脑中信息的传递依赖于无数穿梭不息的“信使”,在控制我们身体运动的区域,最重要的信使之一是多巴胺 (dopamine)。然而,在帕金森病 (Parkinson's disease, PD) 患者的大脑中,负责生产多巴胺的神经元工厂,位于黑质致密部 (substantia nigra pars compacta) 的细胞,正在逐渐凋亡。信使的减少导致运动控制网络陷入混乱,表现为我们所熟知的震颤、僵硬和行动迟缓。
数十年以来,我们对抗帕金森病的主要策略,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脑深部电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都更像是“交通疏导”,它们能缓解一时的拥堵,却无法阻止神经元工厂的持续倒闭。我们能否另辟蹊径,不再仅仅是修补,而是进行重建?直接补充新的、能生产多巴胺的细胞,就如在废弃的工厂旧址上重建一座崭新的生产线,这便是细胞替代疗法 (cell replacement therapy) 的核心思想。
这个看似科幻的设想,如今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10月3日,《Cell》的研究报道“Phase 1/2a clinical trial of hESC-derived dopamine progenitors in Parkinson’s disease”,详细报道了一项利用人胚胎干细胞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hESCs) 衍生的多巴胺能祖细胞 (dopaminergic progenitors) 治疗帕金森病的I/IIa期临床试验结果。这项研究不仅为我们展示了这项疗法的安全性,更在疗效上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初步证据,为无数患者和家庭点燃了新的希望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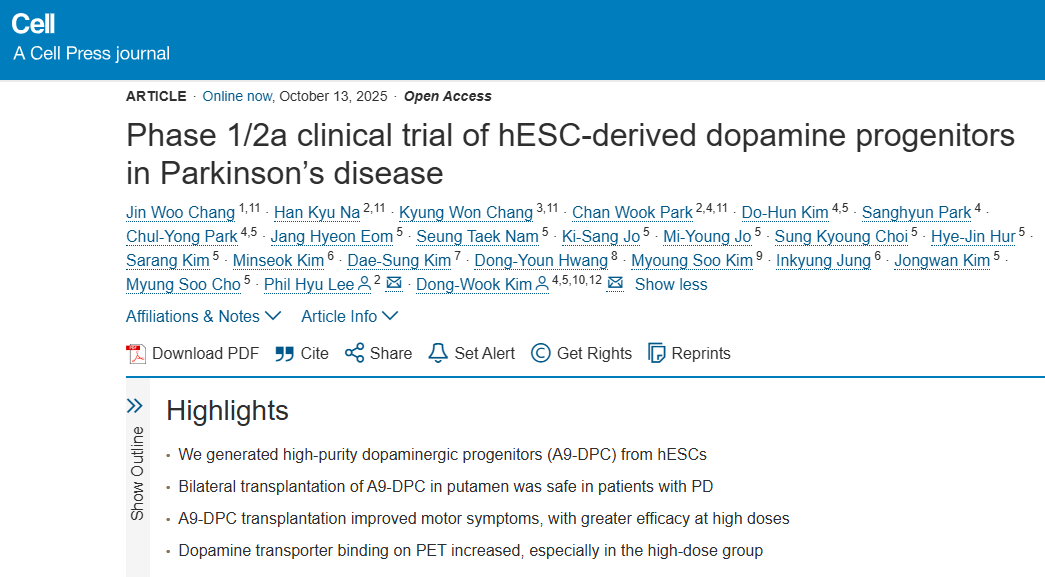
播下一粒种子:如何从源头定制一颗“多巴胺新星”?
一切伟大的重建,都始于一粒优质的种子。对于细胞疗法而言,这粒“种子”就是用于移植的细胞。它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治疗的成败,甚至患者的安危。如果细胞纯度不够,可能混入其他类型的细胞,导致无法预料的副作用;如果细胞有不受控制的增殖潜力,更可能形成肿瘤。因此,在走向临床之前,研究人员必须首先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大规模、高标准地生产出我们需要的特定细胞,A9型中脑多巴胺能祖细胞 (A9-type dopaminergic progenitors, A9-DPC)?
这正是这项研究的第一个巧妙之处。研究团队建立了一套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 的标准化生产流程。他们从一个经过临床级别认证的人胚胎干细胞系 (SNU-hES32) 出发,利用一套完全不含动物源成分、仅由几种“小分子化合物”构成的培养体系,对其进行精准的定向诱导分化。
这个过程就像是为干细胞规划了一条精准的成长路径。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两种小分子抑制剂:Dorsomorphin (DM) 和 SB431542 (SB),进行“双SMAD信号通路抑制 (dual SMAD inhibition)”。这一步的目的是阻断干细胞向其他谱系(如内胚层、中胚层)分化的“岔路”,强制性地将它们推向成为神经细胞的“主干道”。随后,细胞被培养成三维的细胞团块,在悬浮状态下进一步接受这种“神经引导”。
当细胞确认了自己“神经世家”的身份后,下一步就是区域特化,告诉它们不仅要做神经元,还要做“中脑区域”的“多巴胺”神经元。这时,另外两种小分子激动剂:Smoothened Agonist (SAG) 和 CHIR99021 (CHIR) 登场了。它们分别激活了Sonic Hedgehog (SHH) 和 Wnt 这两条对中脑多巴胺神经元发育至关重要的信号通路。通过对这些信号进行精细的时间和浓度调控,研究人员成功地将这些神经祖细胞塑造成了我们最终需要的中脑多巴胺能祖细胞。
在分化的第19天,这些细胞被大量收获并冷冻起来,建立了一个“工作细胞库 (Working Cell Bank, WCB)”。当临床试验需要时,再从库中取出一部分细胞,经过解冻和最后的成熟培养,最终在第25天成为可以移植的终产品:A9-DPC。整个过程历时超过一个月,每一步都伴随着严格的质量控制检测,包括细胞形态、数量、活性、遗传稳定性、身份、纯度乃至无菌和无污染检测。只有通过所有预设标准的产品,才能被最终用于患者移植。这种“订单式生产”和严格的质控,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移植细胞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精准“滴灌”:当细胞疗法遇上神经外科手术
有了高质量的“种子”,接下来就是如何将它精准地“播种”到大脑这片需要修复的“土壤”里。这项研究采用的是一项单中心、开放标签 (open-label)、剂量递增 (dose-escalation) 的I/IIa期临床试验设计。这种设计在探索性新疗法的早期临床研究中非常常见,其首要目标是评估安全性,其次才是初步探索其有效性。
研究共招募了12名中度至重度的帕金森病患者,他们的病程均超过5年,平均年龄约为60.3岁。这些患者被分为两个队列,每个队列6人:
低剂量组 (Low dose cohort):接受双侧大脑壳核 (putamen) 共移植315万个A9-DPC细胞。
高剂量组 (High dose cohort):接受双侧大脑壳核共移植630万个A9-DPC细胞。
为什么选择壳核作为移植靶点?因为在帕金森病中,壳核是多巴胺缺失最严重的区域,与运动症状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通过将新的多巴胺能细胞移植到这里,研究人员希望能够最直接地重建局部的多巴胺供应。
手术过程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在神经外科医生的主刀下,借助先进的立体定向技术 (stereotactic techniques) 和手术计划软件,研究人员为每位患者的壳核设计了多条注射轨迹。每个半球有3条主要轨迹(前、中、后),每条轨迹上又分布3个注射点,总计每个患者的大脑中共有18个微小的细胞沉积点。这种“网格化”的播种方式,旨在让细胞尽可能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壳核区域,以实现最大范围的功能覆盖。
当然,将“外来”的细胞植入大脑,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所有参与试验的患者都接受了为期12个月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使用的药物包括巴利昔单抗 (basiliximab)、他克莫司 (tacrolimus) 和糖皮质激素等,这与器官移植中使用的方案类似,目的是为移植的细胞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温室环境”,让它们能够顺利存活、整合并发挥作用。
从细胞的制备到最终的移植,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未知。现在,种子已经播下,接下来就是长达一年的密切观察,所有人都屏息以待:这些新生的细胞,究竟能否在大脑中安家落户,并带来期待中的改变?
安全第一道岗:移植的细胞在脑内“安分守己”吗?
对于任何一项首次进入人体的创新疗法,尤其是干细胞疗法,安全性永远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长达12个月的随访期内,研究人员对12位患者进行了严密的监控,记录所有发生的不良事件 (Adverse Events, AEs)。
结果令人松了一口气。在记录到的32起不良事件中,经过研究者的严格评估,没有任何一起被认为与移植的A9-DPC细胞本身直接相关。这意味着,在12个月的观察期内,没有出现人们最担心的肿瘤形成、细胞异常增生或异位迁移等情况。脑部磁共振成像 (MRI) 扫描也证实了这一点,除了手术针道留下的预期信号改变外,移植区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占位性病变。
当然,整个治疗过程并非毫无波澜。有1起不良事件与手术操作相关:一位患者在术后CT扫描中发现右侧尾状核有无症状的微小出血,这种情况在脑部穿刺手术中有一定的发生率,且该患者并未因此产生任何临床症状。
另外,有3起不良事件被认为可能与免疫抑制药物相关。其中一位患者出现了短暂的高钾血症,经过药物治疗后迅速缓解。另一位患者在术后6个月被诊断为新发糖尿病,并开始接受口服降糖药治疗;同时,这位患者在术后3个月出现了血小板减少症,虽然因此延长了一天住院时间而被记为“严重不良事件 (Serious Adverse Event, SAE)”,但患者本人始终没有症状,血小板计数也随着密切观察逐渐恢复正常。
总体来看,这项试验的安全性数据是相当积极的。它表明,经过严格GMP标准生产的A9-DPC细胞,通过立体定向手术移植到帕金森病患者的壳核中,是安全且可耐受的。虽然免疫抑制药物带来了一些可控的副作用,但这为未来优化免疫抑制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安全性的“绿灯”,为我们进一步审视疗效数据铺平了道路。
唤醒沉睡的身体:数据揭示的运动功能“复苏”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疗效上。这项疗法真的能改善帕金森病的运动症状吗?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系列国际公认的评估量表,其中最核心的是“运动障碍学会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第三部分”(Movement Disorder Society 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 part III, MDS-UPDRS part III),它由临床医生对患者的运动功能进行专业评估,分数越高代表障碍越严重。评估在患者停用抗帕金森药物12小时后的“关”期 (OFF-medication state) 进行,以排除药物的干扰,更真实地反映疗法本身的效果。
12个月后,激动人心的数据浮出水面。
在“关”期状态下,12名患者的MDS-UPDRS Part III平均分从基线的59.3分下降到了45.2分,平均改善了14.1分。这是一个具有临床意义的显著改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善表现出了明显的剂量依赖性:
低剂量组:平均分数从61.0分下降到48.3分,改善了12.7分。
高剂量组:平均分数从57.7分下降到42.2分,改善了15.5分。
统计学分析显示,高剂量组的改善趋势在整个12个月的观察期内显著优于低剂量组 (p = 0.019),这为疗效的真实性提供了更强的证据:更多的细胞带来了更好的效果。在12名患者中,有11人的运动功能得到了改善。
除了MDS-UPDRS评分,其他指标也呈现出一片向好的景象。例如,反映疾病整体严重程度的Hoehn and Yahr (H&Y)分期,在“关”期状态下也得到了改善。更贴近患者日常生活的指标是“关期”时间的记录。在治疗前,患者每天(按16小时清醒时间计)平均有7-8小时处于药物失效的“关”期,生活质量大受影响。治疗12个月后:
低剂量组:每日平均“关期”时间从7.56小时减少到3.92小时,缩短了近一半。
高剂量组:每日平均“关期”时间从8.41小时减少到5.40小时,减少了约3小时。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患者生活质量的真实提升,更多的“开”期时间意味着他们能够更自由地活动、更好地自理生活。此外,包括非运动症状、生活质量问卷在内的多项评估,也都显示出积极的改善。
有趣的是,在患者正常服药的“开”期 (ON-medication state),MDS-UPDRS Part III分数并没有显著改善。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细胞替代疗法的价值,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基础性多巴胺补充,尤其是在药物效果减退的“关”期,它起到了“托底”的作用,平抑了患者运动状态的剧烈波动。这些数据共同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移植的细胞似乎真的开始工作了,它们正在为患者“沉睡”的身体注入新的活力。
“点亮”大脑:PET扫描下的微观重建现场
临床症状的改善固然令人鼓舞,但作为严谨的科学探索,我们还需要更客观的证据。这些移植的细胞真的存活下来,并且分化成了能够释放多巴胺的神经元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动用了一项强大的“可视化”武器:18F-FP-CIT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18F-FP-CIT是一种可以与多巴胺转运体 (dopamine transporter, DAT) 结合的显像剂。DAT是多巴胺能神经元末梢上的一个标志性蛋白,负责回收突触间隙的多巴胺。因此,通过PET扫描检测到18F-FP-CIT信号的强度,就可以间接反映出功能性多巴胺能神经末梢的密度。信号越强,说明健康的多巴胺能神经元越多。
在移植前和移植后12个月,所有患者都接受了PET扫描。结果呈现出一种引人深思的模式:
在未接受移植的尾状核 (caudate nucleus),12个月后DAT信号普遍出现了下降,中位降幅约为9%。这符合帕金森病自然进展过程中多巴胺能神经元持续退化的规律。
然而,在接受了细胞移植的壳核后部 (posterior putamen),也就是多巴胺缺失最严重、功能重建最关键的区域,DAT信号发生了逆转性的增加!
这种增加同样表现出剂量效应:
低剂量组:壳核后部的DAT信号中位变化为增加1.0%。
高剂量组:壳核后部的DAT信号中位变化为增加10.7%!
尤其是在与运动功能最密切相关的背侧壳核后部,高剂量组的DAT信号增加与低剂量组相比,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p = 0.041)。这幅“点亮”大脑的影像学画卷,为细胞的存活和功能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在体证据。
最关键的一步,是将影像学上的变化与临床上的改善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发现,壳核后部DAT信号增加越多的患者,其MDS-UPDRS Part III运动评分(排除震颤后)的改善也越显著 (Spearman相关系数 ρ = -0.594, p = 0.046)。这条证据链的闭合,极大地增强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不仅仅是患者“感觉”好转了,我们还能通过影像“看见”他们大脑中正在发生的积极生物学改变,并且这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关联。这表明,移植的A9-DPC细胞不仅活了下来,还成功地分化、成熟,并整合进了宿主的大脑神经环路中,开始执行它们作为“多巴胺信使”的使命。
在希望之光下,我们还需看见什么?
面对如此振奋的结果,我们既要拥抱希望,也要保持科学的审慎。这项研究本身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在论文中也进行了坦诚的讨论。
首先,这是一项样本量较小 (12人) 且开放标签的研究。开放标签意味着医生和患者都知道接受了何种治疗,这无法排除“安慰剂效应 (placebo effect)”的潜在影响。帕金森病领域的安慰剂效应尤其显著,仅仅是期待本身,有时就能带来暂时的症状改善。
然而,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反驳论点。他们指出,在以往多个帕金森病的临床试验中,安慰剂组患者的18F-FP-CIT PET扫描结果无一例外都显示DAT信号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这反映了疾病的自然进展。而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观察到的是移植区域DAT信号的明确增加,这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逆转,是安慰剂效应极难解释的。
其次,这是单中心的研究,所有患者都来自同一族裔背景(韩国)。未来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群中验证其普适性。
第三,随访时间目前为12个月。虽然结果喜人,但细胞替代疗法的长期稳定性和安全性仍需更长时间的观察。尤其是在停用免疫抑制剂后,移植物能否与宿主免疫系统“和平共处”,避免迟发的免疫排斥,是未来研究的关键。为此,该试验计划对患者进行长达5年的长期随访。
此外,将这项研究置于全球细胞治疗研究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也很有意义。近期,另外两项分别使用hESC(产品名为bemedaneprocel)和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 的帕金森病细胞治疗临床试验也公布了结果。三者在细胞来源(本研究使用新鲜制备的细胞,而bemedaneprocel使用冷冻的“现货型”产品)、移植剂量、靶点覆盖范围以及患者基线严重程度上都存在差异。例如,本研究的受试者在入组时的疾病程度相对更重。这些差异使得直接比较变得困难,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宝贵的探索经验,为后续临床试验的设计提供了多维度的参考。
从临床试验到“货架上的药物”,还有多远?
这项发表于《细胞》的临床试验,无疑是帕金森病治疗领域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系统地展示了从高质量细胞制备到精准移植,再到安全性和有效性验证的全过程,用详实的数据证明了hESC衍生细胞替代疗法的巨大潜力。
重建大脑中失去的多巴胺能神经系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通过移植新的细胞,我们不仅有望改善患者的运动症状、减少“关”期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更有可能从生物学层面上延缓甚至部分逆转神经退行的进程。这与现有治疗手段形成了本质区别,是从“对症”向“对因”迈出的关键一步。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一项成功的早期临床试验,到成为一种人人可及的、标准化的“货架上的药物”,依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接下来的核心任务,是开展更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placebo-controlled) 的III期临床试验。只有通过这样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检验,才能最终确认其确切疗效,并将其写进临床指南。同时,长期随访将揭示疗效的持久性,并为优化免疫抑制方案提供依据,我们甚至可以畅想,未来是否能通过基因工程等手段诱导免疫耐受,让患者摆脱长期服药的负担。
成本和可及性也是必须考量的现实问题。干细胞疗法的制备和移植过程复杂且昂贵,如何降低成本,让更多的普通患者能够受益,将是技术转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战。
尽管前路漫漫,但这项研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面对帕金森病这片曾经看似只能不断沙化的“焦土”,我们或许真的有能力通过播撒细胞的“种子”,重建一片生机盎然的“多巴胺绿洲”。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