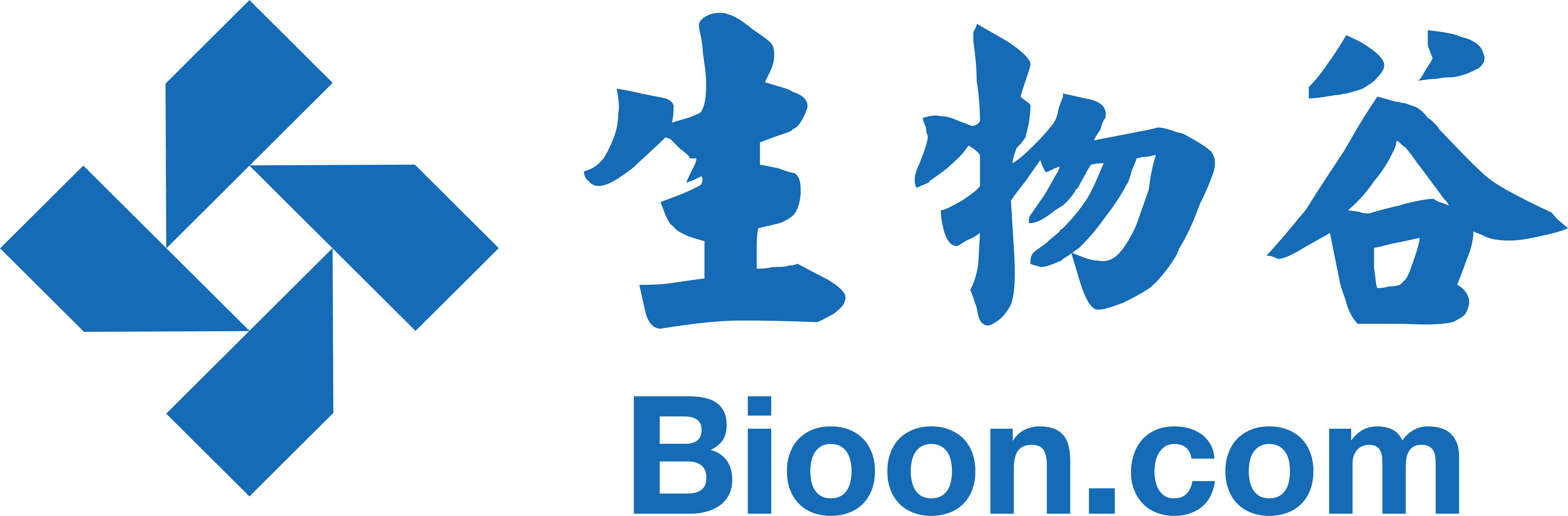Science :穿越百年的质粒狩猎:在抗生素时代之前,细菌的军火库里藏着什么? 游离的DNA 生物探索 2025年12月9日 16:36
来源:生物探索 2025-12-11 17:02
阻断质粒的融合、抑制质粒的接合转移,或者是寻找能够破坏多复制子质粒稳定性的方法,或许是未来打破细菌耐药性僵局的关键。
在人类与微生物的漫长博弈中,我们往往聚焦于致命病原体或抗生素耐药基因(AMR genes)。然而,运送这些“武器”的载具:质粒(Plasmids),其百年进化史却鲜为人知。

想象一下,如果耐药基因是子弹,那么质粒就是那辆装甲车。
2019年,全球有超过 495万人 死于与抗菌素耐药性感染相关的疾病。面对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对于“子弹”的种类已经了如指掌,但对于“装甲车”是如何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从简陋的运输板车进化为如今坚不可摧、火力全开的超级战舰,我们的认知却惊人地匮乏。
这一认知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缺乏一块“罗塞塔石碑”,我们需要一组来自抗生素大规模使用之前的细菌样本,来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被抗生素淹没之前,质粒究竟长什么样?这不仅仅是一次考古,更是一次对未来危机的深刻预警。
默里这一家的“时间胶囊”
故事的起点,是一个名为“默里收藏”(Murray Collection)的生物样本库。
这是一个由数百株致病性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细菌组成的独特集合。它们并非来自现代的实验室,而是分离自 1917年至1954年 间的患者。这段时间,恰好处于人类发现并开始治疗性使用抗生素的黎明期,跨越了抗生素时代的“前夜”到“清晨”。对于研究人员而言,这简直是一座埋藏了近百年的金矿。
在这项浩大的工程中,研究人员对默里收藏中的 368个基因组 进行了深入挖掘。为了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他们不仅仅依赖于短读长的Illumina测序,还对其中 26% 的样本进行了长读长测序(Long-read technologies),从而生成了 218个高质量的混合组装质粒(Hybrid assemblies)。
这些混合组装数据至关重要,因为质粒结构中往往充满了重复序列,长读长技术如同在迷宫上空架起了一座桥梁,让我们看清了质粒完整的环状结构。
最终,研究人员从默里收藏中重建了765个质粒,并将它们与公共数据库中来自全球79个国家、6大洲的 40,757个 现代质粒基因组进行了比对。这构建了一个包含 9,951个 关键质粒的庞大网络,通过构建序列相似性网络,研究人员将这些质粒划分为了940个“近亲家族”(Close Families, CFs)。正是基于这些家族的兴衰更替,我们才得以看清这百年间发生的剧变。
纯真年代:那个没有武器的旧世界
如果让你穿越回1920年,你会发现那时的质粒世界显得格外“清澈”和“单纯”。研究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前抗生素时代(PAE)质粒,根本不携带任何耐药基因。
在那个没有抗生素选择压力的年代,质粒的主要功能并非抵御药物,而是可能携带一些生物合成相关的基因,或者是仅仅维持自身的复制与传递。研究人员定义了三类质粒家族:完全由PAE质粒组成的“PAE-CFs”、完全由现代质粒组成的“Modern-CFs”,以及两者混合的“Mixed-CFs”。
而在那些完全属于旧时代的家族(PAE-CFs)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残酷的进化淘汰。这些家族约占所有PAE质粒的 23%(184个),然而,自1954年之后,它们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公共质粒数据库中出现过。换句话说,这些古老的质粒谱系在进化的长河中“灭绝”了。
这引发了我们深层的思考:为什么这四分之一的质粒会消失?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携带质粒是有成本的(Fitness cost)。在没有外部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质粒不能给宿主带来明显的生存优势,它就很容易在繁衍的过程中被丢弃。
但并非所有的旧时代质粒都遭遇了灭顶之灾。事实上,大部分(77%)的PAE质粒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它们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质粒多样性的基石,这便是研究中提到的“混合家族”(Mixed-CFs)。
保守的幸存者:以不变应万变
混合家族(Mixed-CFs)是这场百年进化实验中的“中流砥柱”。它们包含了数据集中 60% 的质粒,代表了那些从1917年一直延续到2020年甚至更久的古老血脉。
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幸存者表现出了一种极强的“保守性”。泛基因组分析显示,95% 的混合家族拥有一个核心基因组(Core genome)。这意味着,在长达百年的时间跨度里,尽管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质粒依然顽强地维持着它们的基本骨架。
但是,生存并非一成不变。为了在抗生素时代活下去,这些保守的质粒也做出了妥协。数据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在混合家族中,那些存活至今的现代后代,如果获得了耐药基因(AMR positive),它们的体型往往比那些没有获得耐药基因的“兄弟姐妹”要大。
携带耐药基因的混合家族质粒平均大小:71.4 kb
不携带耐药基因的质粒平均大小:21.7 kb
(差异显著,P = 1.292e-09)
此外,这些获得了耐药能力的幸存者,其核心基因组的比例显著降低(平均12.3% vs 39.3%),这意味着它们为了容纳新的基因(比如耐药基因、转座子和整合子),牺牲了部分基因组的稳定性。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超级质粒的诞生
这是本项研究中最令人不安,也最发人深省的发现。除了那些保守的混合家族,研究人员还鉴定出了一类完全由现代质粒组成的家族——“现代家族”(Modern-CFs)。虽然它们只占数据集中质粒总数的22%,但它们却携带了整个网络中 50%的耐药基因。
如果说混合家族是装备了防弹背心的老兵,那么现代家族就是全副武装的机械战警。这些现代质粒并非凭空产生,它们“吞噬”了旧时代的质粒。数据表明,约98%(3,646个)的现代家族质粒包含与至少一个PAE质粒匹配的序列。
这些包含PAE序列的现代质粒,其体积是它们所包含的PAE质粒的 12倍。这不再是简单的“进化”,这是一种“融合”。现代质粒通过一种被称为“共整合”(Cointegration)的过程,将多个不同的质粒骨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多复制子(Multi-replicon)的嵌合体。
在这些庞然大物中,58% 的质粒携带多个复制基因(rep genes),而PAE质粒中这一比例仅为17%。这种融合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它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移动基因库。研究中提到了一些极端的例子,例如质粒 pSY3626C1 和 pHZ003,它们单个质粒上就分别携带了针对 8种 和 13种 不同药物类别的耐药性,其中甚至包括多达 40个 独立的耐药基因!
进化的机制:出生、死亡与选择的炼金术
面对这些结构复杂、体积庞大的现代质粒,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进化的动力是什么?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基于“出生-死亡”(Birth-Death)过程的模型。在没有抗生素的世界里,融合产生的巨大质粒因为高昂的代谢成本而不稳定,往往在诞生后不久就会崩解。
然而,抗生素引入了强烈的正选择压力。在这个新世界里,生存的法则变了。抗生素就像是一种强力的胶水,将那些原本松散、不稳定的遗传元件强行粘合在一起。研究人员通过四个定性测试验证了这一理论:
1 历史的痕迹
在PAE时期,多复制子质粒虽然少(17%),但确实存在,说明融合机制在抗生素使用前就已经就位。
2 碎片的命运
没有任何一个PAE家族的质粒以其原始形式完整地出现在现代数据库中,它们要么灭绝,要么作为碎片嵌入到更大的现代质粒中。
3 选择的印记
在存活下来的混合家族中,那些携带耐药基因的质粒往往拥有更多的耐药基因拷贝,这表明多样性是被选择出来的,而非随机漂变。
4 动态的快照
现代家族主要由小的家族群和“单身汉”组成,表明这些巨大的质粒处于高度动态的生成和消亡过程中。
阴阳两界:革兰氏阴性菌与阳性菌的殊途
在构建这个宏大的质粒网络时,研究人员还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涉及细菌分类学中的两大阵营:革兰氏阴性菌(Gram-negative)和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默里收藏主要由肠杆菌科(革兰氏阴性菌)组成。研究发现,这些细菌的质粒进化与一种名为“接合”(Conjugation)的机制紧密相关。数据表明,在现代家族和混合家族中,携带耐药基因的质粒大部分(分别为58%和51%)都属于接合型质粒,且往往体积更大。
然而,当研究人员将视野扩展到与默里质粒无亲缘关系的革兰氏阳性菌质粒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它们同样表现出耐药基因聚集的现象,但并不像革兰氏阴性菌那样依赖于接合机制。
尽管传播方式有所不同,但有一个特征在两大阵营中是通用的:多复制子状态。这再次印证了“融合”是驱动超级质粒形成的核心机制,也是跨越菌种界限的通用进化策略。
这一百年的进化课:我们学到了什么?
回顾这篇发表于《Science》的研究,我们仿佛在看一部微观世界的史诗电影。从1917年到2025年,我们目睹了质粒从“小而美”的纯真年代,演变成了如今“大而全”的耐药堡垒。这项研究最为深刻的启示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活动(工业化抗生素使用)是如何不仅改变了细菌的基因内容,更是重塑了细菌遗传信息的组织形式。
研究数据告诉我们,现代融合质粒仅占总数的22%,却承载了 50% 的耐药基因负担。这是一个极其高效且危险的比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多重耐药细菌(MDR bacteria)如此难以根除——它们体内的质粒不再是单一的遗传分子,而是一个动态的、模块化的系统。
对于未来的抗生素耐药性治理,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如果我们只盯着耐药基因本身,可能永远无法跟上细菌进化的步伐。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些载体——质粒的进化动力学。阻断质粒的融合、抑制质粒的接合转移,或者是寻找能够破坏多复制子质粒稳定性的方法,或许是未来打破细菌耐药性僵局的关键。
正如默里收藏在尘封百年后为我们揭示了过去,今天的我们,也正在书写着下一个百年的微生物历史。但愿当我们回望今天时,留下的不仅仅是关于“超级细菌”的恐怖记录,还有人类智慧应对这场危机的勇气与巧妙。
Cazares A, Figueroa W, Cazares D, Lima L, Turnbull JD, McGregor H, Dicks J, Alexander S, Iqbal Z, Thomson NR. Pre- and postantibiotic epoch: The historical spread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cience. 2025 Dec 4;390(6777):eadr1522. doi: 10.1126/science.adr1522. Epub 2025 Dec 4. PMID: 40997220.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