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IBD百年“全球迁徙”,揭示肠道疾病演变四大阶段
来源:生物探索 2025-05-05 15:31
IBD的传播和爆发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可预测的、跨越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流行病学模式。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长期以来被视为北美和欧洲等早期工业化地区的“西方病”。然而,4月30日发表在《Nature》上的最新研究“Global evolution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cross epidemiologic stages”,用前大量的数据告诉我们:这种认知已经过时了!
这项研究汇集了超过一个世纪(1920-2024年)的数据,覆盖全球82个地区、522项人群研究,堪称IBD流行病学领域的“百年全球档案”。此外,研究团队不仅梳理了发病率(Incidence)和患病率(Prevalence)的历史变迁,更首次利用复杂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算法和数学模型(Mathematical Model),为IBD在全球范围内的演变路径绘制了一张清晰的“进化图谱”。他们发现,IBD的传播和爆发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可预测的、跨越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流行病学模式。
从发病率和患病率都极低的“出现期”(Emergence),到发病率如火箭般窜升、但患病率相对滞后的“加速期”(Acceleration),再到发病率趋稳、但患病人数爆炸式增长的“复合增长期”(Compounding Prevalence),研究量化了每个阶段的特征,并首次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患病率平衡期”(Prevalence Equilibrium)进行了模型预测。这种演变与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西方化”等社会驱动力紧密相连。
IBD这场全球性健康挑战是如何一步步从局部走向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何会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未来的疾病负担会如何演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份研究不仅是一份详实的数据报告,更是一部关于疾病与社会变迁的史诗级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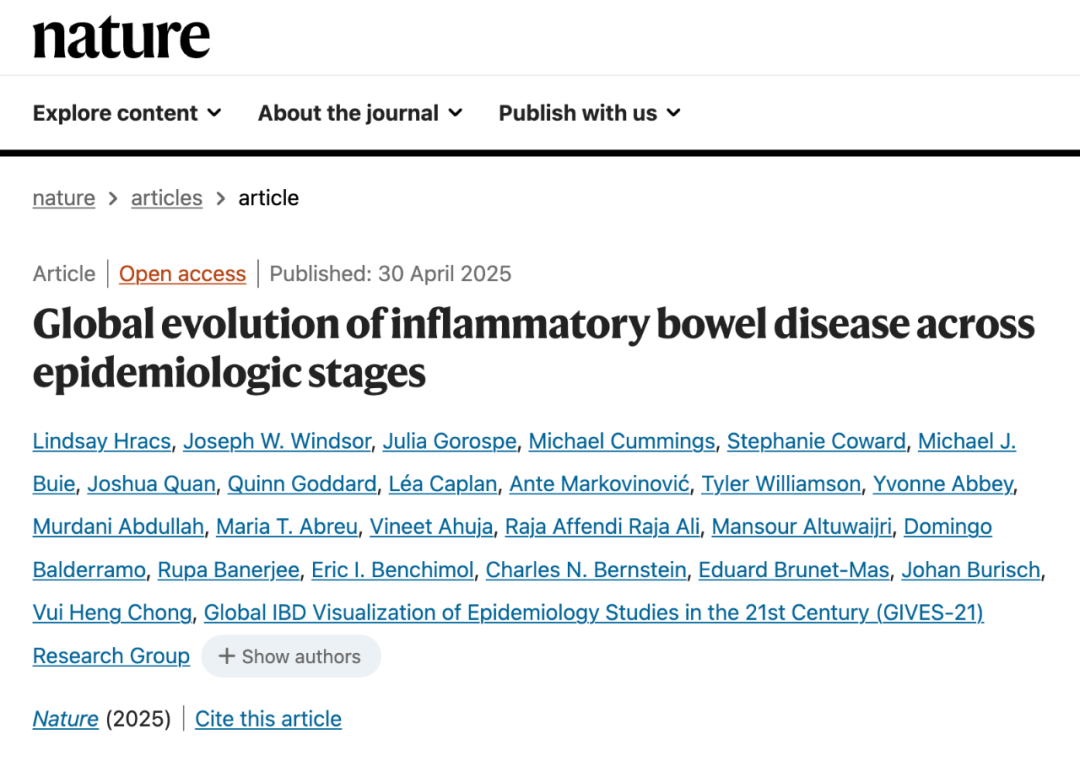
IBD:不再只是“西方病”的肠道困境
长久以来,炎症性肠病(IBD)——一种以慢性、反复发作为特征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常常被认为是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早期工业化地区(Early Industrialized Regions)的“专属”疾病。在20世纪早期,IBD在这些地区被视为罕见病,主要影响欧洲移民的后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Second World War)之后,这些早期工业化地区的IBD发病率(Incidence Rate)开始快速上升。
数据显示,在美国,克罗恩病(CD)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病率合并范围(Coalescing Range, CR,研究中使用25%-75%分位数表示)为1.15-2.30(每10万人年),溃疡性结肠炎(UC)为1.02-2.41。到了50年代,欧洲的IBD发病率也开始升高,瑞典的UC发病率CR为1.88-7.50,CD为0.97-2.18。这些数字虽然今天看起来不高,但在当时已经代表了显著的增长趋势。
进入21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IBD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世界”。研究指出,在新兴工业化地区(Newly Industrialized Regions)和欠发达地区(Emerging Regions),IBD的发病率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虽然在非洲等欠发达地区,IBD病例仍然相对零星,但亚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工业化地区的IBD发病率,特别是UC,呈现出急剧增加的趋势。
以日本为例,这个较早进入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其IBD流行病学数据变化尤为突出。数据显示,在日本,上世纪70年代之前,IBD的发病率低于0.25,但到了1980年已经超过0.4。到2000年,UC的发病率飙升至4.77,CD发病率也达到1.27,相较于早期增长了十倍。韩国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80年代发病率很低(CD的CR为0-0.03,UC为0.21-0.33),但到了2010年代,CD的CR升至2.20-3.20,UC升至4.11-6.27。这些数据表明,IBD的流行范围正在全球蔓延,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挑战。
IBD从一个地区性罕见病转变为全球性健康问题,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其流行病学模式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研究团队认为,IBD的流行病学演变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一套可被量化的、跨越不同阶段的规律。
解码IBD的“进化论”:四大流行病学阶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IBD在全球的演变,研究团队提出了IBD流行病学的“四阶段”理论,并首次尝试使用实际数据为这些阶段设定定量基准。这四个阶段分别是:
阶段1:出现期(Emergence):这个阶段的特点是IBD发病率和患病率(Prevalence,指每10万人中患病总人数)都很低。IBD可能零星出现,但尚未被广泛识别和诊断。研究中机器学习模型分类的阶段1数据显示,CD的CR-I(发病率合并范围)为0.1-1.2,CR-P(患病率合并范围)为1.2-10.5。UC的CR-I为0.1-1.2,CR-P为1.2-10.5。这个阶段代表了IBD在一个地区开始被认识、但总体负担很轻的状态。
阶段2:加速期(Acceleration):进入这个阶段,IBD的发病率开始快速上升,呈逐年加速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发病时间不长,患病率仍然相对较低。这个阶段通常与社会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加速有关。该研究中机器学习模型分类的阶段2数据显示,CD的CR-I飙升至3.3-10.6,UC的CR-I也达到3.3-10.6。而患病率虽然有所增长,但相比发病率仍处于较低水平,CD的CR-P为31.2-100.5,UC的CR-P为31.2-100.5。巴西就是拉丁美洲进入加速期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在2000年代的发病率快速增加,2010年代CD的CR-I达到1.21-3.22,UC的CR-I达到2.42-5.66。
阶段3:复合增长期(Compounding Prevalence):在这个阶段,IBD的发病率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可能趋于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但由于之前几十年的发病积累,且IBD通常不致命,患病率持续并快速攀升,患病人数不断增加,给医疗系统带来沉重负担。机器学习模型分类的阶段3数据显示,CD的CR-I为18.1-34.1,UC的CR-I为18.1-34.1,发病率范围相比阶段2有所提升但增长速度放缓。而患病率则急剧攀升,CD的CR-P达到362.9–660.1,UC的CR-P也达到362.9–660.1。许多早期工业化地区,如北欧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例如丹麦,2010年代UC发病率CR高达22.21-30.64,是全球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其患病率也在持续高位增长。
阶段4:患病率平衡期(Prevalence Equilibrium):这是一个理论上存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IBD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大致平衡,使得患病率的增长速度放缓并最终达到稳定甚至平台期。这个阶段的实现可能与人口老龄化、IBD患者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等因素有关。到目前为止,研究数据尚未明确证实有地区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但数学模型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其发生的可能性。
研究团队利用包含来自全球82个地区、跨越1920年至2024年一个多世纪的522项基于人群的研究数据,构建了一个机器学习分类器,以准确识别每个地区在不同时间点所处的流行病学阶段。这个模型不仅能够自动化分类,还能为各阶段的发病率和患病率设定具体的“门槛”值(即上述的CR范围),这对于理解IBD在全球的演变至关重要。机器学习模型在未见过的数据集上表现出了高达95.15%的分类准确率,证明了该阶段划分方法的有效性。
地图上的变迁:IBD的全球迁徙足迹
研究团队通过全球地图可视化,生动地展示了IBD流行病学阶段在全球范围内的时空演变。
回溯到20世纪中期(1950-1959年),地图显示IBD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少数早期工业化地区,这些地区正从阶段1向阶段2过渡或已经进入阶段2。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则处于数据匮乏的阶段,推测应处于阶段1。
到了20世纪后期(例如1980-1989年),早期工业化地区的颜色加深,表明它们普遍进入了发病率快速上升的阶段2,部分地区可能开始迈入阶段3。同时,日本等一些较早进入工业化的亚洲国家也开始显现出阶段2的特征。
进入21世纪(例如2010-2019年),全球IBD的流行病学图景发生了显著变化。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处于阶段3,这意味着这些地区IBD的患病人数在持续快速增加。而包括中国、韩国、巴西在内的许多新兴工业化地区则步入了阶段2,发病率正在迅速攀升。非洲和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数据依然相对稀疏,但部分地区可能处于阶段1或开始显现向阶段2过渡的早期迹象。
这张不断变化的全球地图,描绘了IBD如何从少数地区的“风暴”眼,逐渐蔓延扩散,影响到全球越来越多的人群。它告诉我们,IBD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印证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趋势。
阶段背后的推手: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子”
IBD流行病学阶段的变迁并非无源之水,而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变迁以及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研究团队深入探究了不同流行病学阶段背后的驱动因素,发现了一系列与阶段转变显著相关的社会指标。
该研究分析了五项关键的社会指标在不同流行病学阶段的表现:增强人类发展指数(Augmented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HDI)、肥胖率(Obesity Rate)、城镇化率(Percentage Urbanization)、全民健康覆盖服务指数(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Service Index, UHC)和西方饮食指数(Western Diet Index, WDI)。结果显示,这些指标在三个流行病学阶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
例如,以0-1评分的AHDI(衡量教育、预期寿命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为例,阶段1地区的AHDI中位数为0.39,阶段2地区的中位数为0.53,而阶段3地区的中位数为0.70。这表明IBD流行病学阶段的演进与一个地区整体的人类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欠发达走向更发达。
同样,肥胖率也呈现出随阶段递增的趋势,阶段1的中位数为7.70%,阶段2为15.30%,阶段3为18.30%。城镇化率也从阶段1的中位数39%增加到阶段3的70%。UHC指数和西方饮食指数也显示出类似的正向关联,阶段1的中位数分别为63.10和0.39,阶段3的中位数分别为80.94和0.55。
这些数据有力地支持了“西方化”(Westernization)假说,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高脂、高糖、精加工食物增加,即“西方饮食”)、卫生条件(过度清洁减少早期微生物暴露)以及环境暴露(污染、工业化学物质等)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宿主的遗传易感性,改变肠道微生物组(Gut Microbiome)和免疫反应,最终导致IBD发病率的上升。
此外,IBD确诊病种比例(UC:CD Ratio)在不同阶段也有显著差异。数据显示,阶段1的中位数UC:CD比例为3.24:1,阶段2降至1.87:1,阶段3进一步降至1.54:1。这意味着在IBD出现的早期阶段(阶段1),UC的诊断相对更容易(可能与当时诊断手段如乙状结肠镜Sigmoidoscopy为主有关),而CD则可能因其病变位置更隐蔽、诊断更复杂而容易被漏诊或误诊为UC。随着诊断技术(如结肠镜Colonoscopy的普及)和医学认知的提高,CD的诊断率上升,UC:CD比例也随之下降。这种比例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IBD流行病学从“未被发现”到“被充分诊断”的过程。
模型预测未来:憧憬阶段4的到来?
阶段3的特点是患病率的快速攀升,这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理解未来的患病趋势,对于医疗资源的规划至关重要。研究团队利用偏微分方程(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PDEs)构建了数学模型,预测了三个处于阶段3的地区——加拿大、丹麦和苏格兰——未来几十年的IBD患病率变化。
模型基于一个关键假设:未来一段时间内各年龄组的IBD发病率保持稳定,采用近期(加拿大2007-2014年,丹麦和苏格兰2010-2017年)的平均发病率作为基础。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即使发病率稳定,这些地区的IBD患病率在未来几十年仍将持续上升。例如,加拿大IBD患病率从2014年的约0.65%(实际观测值)预计将上升到2025年的0.83%,2035年达到0.96%,2043年达到1.05%。丹麦和苏格兰也呈现类似趋势,丹麦患病率预计从2014年的约0.86%上升到2043年的1.59%,苏格兰预计从2014年的约0.74%上升到2043年的1.51%。
然而,模型也预测,虽然患病率总体上升,但其增长的速度(即斜率)正在逐渐放缓。以加拿大为例,患病率增长斜率从2015年的每年0.018%预计下降到2042年的每年0.010%。丹麦和苏格兰的斜率也呈现下降趋势。这种斜率的减缓是向阶段4——患病率平衡期——过渡的信号。研究团队提出,阶段4的定义是患病率的增长斜率在一个5年周期内降低到接近0%(平均变化±0.01%)。根据模型,在发病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到2042年,加拿大预计将达到这个门槛(2042年的增长斜率为0.010%)。这意味着,即使在最乐观的稳定发病率情景下,IBD患病率要达到平台期,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患病率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主要是由于IBD患者群体的老龄化。随着年龄增长,IBD患者的死亡率也会相应增加。当累积的死亡人数开始接近新增的发病人数时,患病人数的净增长就会变慢,最终导致患病率的稳定。因此,IBD的老龄化人口结构是迈向阶段4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预防:能否加速驶向“平衡期”?
如果阶段4代表了IBD流行病学演变中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因为患病人数趋于稳定,医疗资源规划更容易),那么我们能否通过某种方式加速这一过程呢?模型的结果提示,改变IBD的发病率是关键。
研究团队进一步模拟了不同发病率变化情景下的患病率预测。除了稳定发病率情景(0%年变化),他们还模拟了发病率每年下降2%、下降1%、上升1%和上升2%的情景。结果显示,发病率的微小变化都会对未来几十年的患病率产生显著影响。例如,在发病率每年下降2%的最乐观情景下,加拿大2043年的患病率预计将是0.97%,远低于发病率稳定情景下的1.05%或发病率每年上升2%情景下的1.16%。更重要的是,在发病率每年下降2%的情景下,加拿大的患病率增长斜率在2042年降至0.003%,已经低于定义的阶段4门槛(±0.01%),这意味着通过有效降低发病率,阶段4的到来可以大大提前。
这一发现为IBD的未来管理指明了方向:预防(Prevention)是关键。虽然全面预防IBD目前仍是雄心勃勃的目标,但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针对高危人群的预防策略包括:
干预环境因素: 针对与“西方化”相关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如优化饮食结构(增加膳食纤维、减少加工食品)、改善居住环境等,这些观察性研究表明可能有助于降低CD和UC的发病率。
靶向微生物组: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在IBD发病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饮食、益生菌、益生元甚至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等方式调节肠道微生物组,可能有助于预防IBD或延缓其进展。
识别高危人群和早期干预: 通过生物标志物(Biomarkers),如遗传标记(Genetic Markers)、血清学标记(Serological Markers)或粪便微生物特征等,识别那些有较高风险发展为IBD的个体。对于这些高危人群,可以考虑更积极的干预措施,例如针对特定免疫通路的药物治疗,延迟疾病的发生。这类似于在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中使用Teplizumab或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中使用Abatacept来延迟疾病发生的研究。
因此,将研究重点放在预防策略,降低IBD的发病率,不仅能够减轻未来患病率的累积,更能加速迈向患病率平衡期,从而减轻IBD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健康负担。
全球视野与未来挑战:一场进行中的健康侦察
这份跨越百年、覆盖全球的流行病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IBD的演变。它打破了IBD是“西方病”的传统认知,揭示了IBD在全球范围内的迁徙和扩散规律,并首次提供了量化的阶段定义和过渡基准。
研究强调,理解不同地区所处的流行病学阶段,对于其医疗系统应对IBD负担至关重要。处于阶段2的地区需要加强IBD的识别和诊断能力,提高公众和医务人员的疾病意识,建设医疗基础设施。处于阶段3的地区则面临日益增长的患者群体和患者老龄化带来的复杂挑战,需要建立多学科的综合护理模式,确保患者获得及时、高质量的治疗。
当然,这项研究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历史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尤其是在早期和一些欠发达地区。机器学习模型在数据稀缺或阶段过渡区域的分类可能存在误差。数学模型为了简化计算,没有考虑IBD患者与非IBD人群之间可能存在的死亡率差异(虽然研究表明差异相对较小),也未直接纳入移民因素的影响(虽然移民通常会承担迁入地IBD风险)。这些都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方向。
该研究团队包括国际炎症性肠病研究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OIBD)和全球IBD流行病学可视化研究联盟(Global IBD Visualization of Epidemiology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GIVES-21)的研究人员,正在持续收集和更新全球IBD流行病学数据,特别是来自新兴工业化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高质量人群研究数据。他们的工作,就是一场持续进行中的全球健康“侦察”,为我们揭示IBD未来的发展轨迹,并为全球公共卫生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IBD的全球演变史,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全球化背景下复杂互动的一个缩影。通过将流行病学数据、机器学习和数学模型相结合,这项研究不仅为IBD提供了一个精密的“进化”框架,也为理解其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慢性病提供了借鉴。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科学研究报告,更是一个引发思考的案例:健康问题如何跨越国界、与社会变迁交织,以及数据分析和跨学科合作在全球健康挑战中的巨大潜力。
未来,我们能否通过环境干预和精准预防,改变IBD的流行病学轨迹,加速驶向那个“患病率平衡期”?这有赖于科学的持续探索,有赖于公共卫生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我们每个人对自身健康和环境的关注。这场“肠道风暴”的全球迁徙还在继续,但希望的曙光,也许就在我们对预防和早期干预的不懈追求中。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