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Biotechnology | 颠覆“反义即沉默”旧识:发现广泛存在的天然trans-RNA可激活基因翻译
来源:游离的DNA 2025-11-28 13:43
研究人员不仅通过海量的数据证实了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NSD2 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详实的证据告诉我们:这种致命的身份转换,是可以被逆转的。
在肿瘤学的漫长征途中,我们曾天真地认为,癌症的耐药性主要源于基因突变的积累,就像锁被换了芯,原来的钥匙(药物)自然打不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浮出水面:肿瘤细胞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它们甚至不需要改变基因序列,仅仅通过改变“身份”,就能逃避药物的追杀。
这种现象被称为“谱系可塑性” (Lineage Plasticity)。在压力之下,癌细胞能够通过表观遗传重编程,从一种对药物敏感的细胞类型,转变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对药物耐受的细胞类型。这就像是一个通缉犯,为了躲避追捕,不仅整了容,连指纹(表观遗传修饰)都换了一套。
前列腺癌 (Prostate Cancer) 就是这种“变身术”的集大成者。11月26日,《Nature》的研究报道“NSD2 targeting reverses plasticity and drug resistance in prostate cancer”,为我们揭示了这一过程背后的关键推手,并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逆转策略。研究人员不仅通过海量的数据证实了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NSD2 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详实的证据告诉我们:这种致命的身份转换,是可以被逆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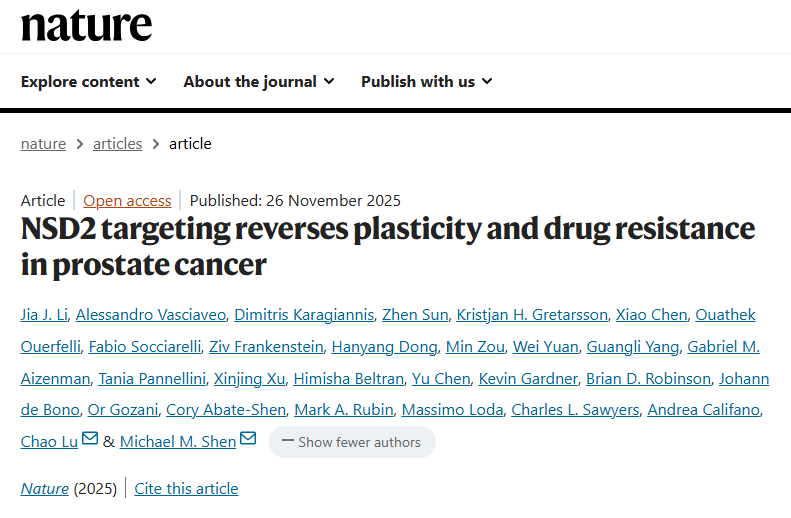
捕捉“变色龙”:在前列腺癌中重现谱系可塑性
要理解这项研究的分量,首先来看看临床上那个令人绝望的困境。对于晚期前列腺癌,目前的标准疗法是使用强效的雄激素受体 (Androgen Receptor, AR) 抑制剂,如恩杂鲁胺 (Enzalutamide)。最初,这些药物效果显著,因为大多数前列腺癌细胞(腺癌)依赖 AR 信号生存。
但是,几乎所有的肿瘤最终都会产生耐药性。在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CRPC) 阶段,约有 5% 到 25% 的病例会发生一种剧烈的“身份转换”:肿瘤细胞丢失了 AR 的表达,不再依赖雄激素,转而表达神经内分泌标记物(如突触素 SYP 和嗜铬粒蛋白 A CHGA)。这种亚型被称为神经内分泌前列腺癌 (CRPC-NE),它不仅对 AR 抑制剂完全免疫,而且侵袭性极强,患者生存期极短。这一过程在原发性肿瘤中极为罕见(小于 0.1%),却在治疗压力下频频发生,暗示了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逃逸”机制。
为了在实验室里捕捉这一稍纵即逝的过程,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巧妙的小鼠模型 (NPp53)。在这个模型中,通过特异性敲除肿瘤抑制基因 Pten 和 Trp53,小鼠的前列腺 luminal 上皮细胞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并自发地经历从腺癌到神经内分泌癌的转分化。
研究人员从 21 只独立的小鼠中建立了类器官 (Organoids) 系。令人惊喜的是,这些类器官完美复刻了人类前列腺癌的异质性。
其中,有 6 个系(命名为 NPPO-1 至 NPPO-6)表现出了明显的神经内分泌特征。更细致的观察揭示了这种异质性的光谱:NPPO-2 几乎全是表达神经内分泌标记物的细胞;而 NPPO-1 和 NPPO-5 则是混合体,既包含表达 AR 的间充质样细胞,也包含神经内分泌细胞;NPPO-4 和 NPPO-6 则更加特殊,它们同时表达 AR 和神经内分泌标记物,呈现出一种“双重人格”的中间状态 (Amphicrine)。
为了看清这些细胞到底在发生什么,研究人员利用单细胞 RNA 测序 (scRNA-seq) 技术,结合 VIPER 算法推断了蛋白质的活性。VIPER 是一种基于调控网络逆向工程的算法,它比单纯的基因表达量更能反映细胞的功能状态。分析结果将这些细胞分成了三个主要簇:簇 1 表现出高干性(CytoTRACE 评分高),表达管腔上皮标记物(如 HOXB13)和间充质标记物(如 VIM),类似于人类的间充质干细胞样前列腺癌;簇 3 则高表达神经内分泌转录因子(如 ASCL1 和 FOXA2),对应 CRPC-NE;而簇 2 则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这种清晰的分类不仅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更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驱动细胞从簇 1 的状态滑向了簇 3 的深渊?
锁定幕后黑手:NSD2 与 H3K36me2 的异常崛起
既然 DNA 序列没有发生剧烈变化,答案一定藏在染色质的修饰上。研究人员对这些具有不同表型的类器官进行了免疫荧光筛选,检查了各种组蛋白修饰水平。在众多的组蛋白标记中,一对“冤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H3K36me2(组蛋白 H3 第 36 位赖氨酸二甲基化)和 H3K27me3(组蛋白 H3 第 27 位赖氨酸三甲基化)。
数据显示,在神经内分泌细胞中,H3K36me2 的水平显著升高,而 H3K27me3 的水平则大幅下降。这不仅发生在小鼠模型中,在人类患者样本中也是如此。对 63 例人类前列腺癌样本的组织微阵列 (TMA) 分析显示,NSD2(负责催化 H3K36me2 的甲基转移酶)在所有的 CRPC-NE 肿瘤中均呈现高表达,而在 33 例未治疗的原发性前列腺癌中却表达较低。
数据显示:在 CRPC-NE 样本中,H3K36me2 高表达细胞的比例显著高于去势抵抗性腺癌 (mCRPC) 样本。更重要的是,NSD2 的高表达与患者的糟糕预后紧密相关。在皇家马斯登医院 (RMH) 的队列(94 例)和前列腺癌基金会 (PCF-SU2C) 的队列(141 例)中,NSD2 高表达的患者总生存期均显著缩短。
NSD2 就像是肿瘤细胞为了“变身”而特意招募的工程师。它的任务是给染色质打上 H3K36me2 的标签。为什么这个标签如此重要?因为 H3K36me2 有一个特殊的生化特性:它能拮抗 PRC2 复合物的活性。
PRC2 复合物是细胞内的“沉默机器”,它负责添加 H3K27me3 修饰,从而关闭基因表达。在正常的腺癌细胞中,PRC2 负责压制那些不该表达的神经内分泌基因。然而,当 NSD2 异常高表达时,大量的H3K36me2 占据了染色质,使得 PRC2 无法结合,H3K27me3 标记随之丢失。这就好比 NSD2 强行撬开了 PRC2 上的锁,释放了被压抑的神经内分泌基因程序。Western Blot 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神经内分泌类器官中,NSD2 和 H3K36me2 水平高企,同时伴随着转录激活标记 H3K27ac 的增加,而 H3K27me3 则几乎消失殆尽。这种表观遗传层面的“此消彼长”,构成了谱系可塑性的分子基础。
逆转时光的实验: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既然 NSD2 是驱动这一过程的元凶,那么,拿掉它,细胞能变回来吗?这不仅是科学上的好奇,更是治疗上的希望。
研究人员利用 CRISPR-Cas9 技术,在神经内分泌类器官(NPPO-1NE 和 NPPO-2)中敲除了 Nsd2 基因。结果是惊人的:显微镜下,原本那些小细胞形态的神经内分泌肿瘤细胞,开始发生剧烈的形态学改变,细胞核质比降低,重新表达了 AR,同时丢失了神经内分泌标记物 CHGA 和 SYP。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机制,研究人员还使用了一种更“巧妙”的手段,表达致癌组蛋白 H3.3K36M。这是一种发生突变的组蛋白,它能像“毒药”一样,显性负调控 NSD 家族及其他甲基转移酶,导致全基因组范围内的 H3K36me2 耗竭。在引入 H3.3K36M 后,原本顽固的 NPPO-4 和 NPPO-6 类器官(那些同时表达 AR 和 NE 标记物的“双面”细胞)也发生了逆转,神经内分泌特征消退,腺癌特征增强。
VIPER 分析清晰地描绘了这一过程:在 Nsd2 被敲除或 H3.3K36M 表达后,细胞群体的分布发生了根本性位移,从代表神经内分泌癌的“簇 2”和“簇 3”,大举向代表腺癌和干细胞样状态的“簇 1”迁移。
这不仅仅是表型的改变,更是基因调控网络的全面重塑。Western Blot 和 CUT&Tag 分析显示,随着 NSD2 的缺失,全基因组范围内的 H3K36me2 信号大幅减弱,而原本被压制的 H3K27me3 信号重新出现。这种表观遗传的“复位”,关闭了神经内分泌基因的表达通道。
更令人兴奋的是,这种逆转不仅发生在小鼠细胞中,在人类 CRPC-NE 类器官(如 MSKPCa10)中也得到了重现。敲除 NSD2 后,这些缺乏 TP53 和 RB1 的恶性人类细胞,同样重新表达了 AR,并在形态上回归腺癌样表型。这意味着,所谓的“终末分化”或恶性进展,并非一条不归路。只要掌握了表观遗传的“开关”,我们完全有机会将癌细胞推回对治疗敏感的状态。
基因组上的“圈地运动”:增强子的争夺战
为了深入解析 NSD2 是如何精准调控这一过程的,研究人员整合了 CUT&Tag(一种高效的染色质分析技术)和单细胞 ATAC-seq 数据。
他们发现,NSD2 介导的 H3K36me2 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形成了一种宽阔的结构域 (Broad Domains)。这些结构域主要覆盖在基因间区和基因体上。在神经内分泌细胞中,正是这些 H3K36me2 结构域的扩张,阻止了 PRC2 复合物的进入,导致 H3K27me3 的丢失。
更有趣的是,这些区域富集了大量的 H3K27ac 信号,这是活跃增强子 (Enhancer) 的标志。通过对这些推定的增强子区域进行基序 (Motif) 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它们富含 ASCL1、FOXA2 和 ONECUT2 等关键神经内分泌转录因子的结合位点。这就像是一场基因组上的“圈地运动”。在 NSD2 的帮助下,H3K36me2 为神经内分泌转录因子圈出了一块块“飞地”,保护其增强子不受 PRC2 的沉默。
具体到基因层面,Chga、Foxa2、Onecut2、Ascl1 和 Mycn 等关键基因的位点上,H3K36me2 信号在神经内分泌细胞中显著富集,而 H3K27me3 信号则呈现互斥的缺失状态。相反,在非神经内分泌细胞中,这些位点则被厚厚的 H3K27me3 “封印”。
通过单细胞 ATAC-seq 进一步分析发现,当 Nsd2 被敲除后,这些神经内分泌特异性增强子区域的染色质开放程度显著下降。这说明,NSD2 不仅是维持 H3K36me2 水平的酶,更是维持神经内分泌转录程序开放状态的守门人。一旦守门人不在,大门关闭,细胞自然无法维持神经内分泌的身份。
破局耐药:小分子抑制剂的临床潜力
科学发现的最终归宿是临床应用。既然 NSD2 是关键靶点,能不能开发出药物来抑制它?虽然 NSD2 曾被认为是一个难以成药的靶点,但科学界从未放弃尝试。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合成了一种名为 NSD2i 的小分子抑制剂(结构类似于处于早期临床试验的 KTX-1001)。
这种小分子展现出了极高的特异性和活性。体外酶活实验显示,NSD2i 抑制核小体上 NSD2 甲基转移酶活性的半抑制浓度 (IC50) 仅为 3.8 nM。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对 NSD2 的选择性是其他甲基转移酶(除 NSD1 外)的 10,000 倍以上。在类器官模型中,NSD2i 的表现堪称完美。处理后的 NPPO-1NE 类器官,H3K36me2 结构域大幅缩减,细胞状态从神经内分泌型向腺癌型转变,典型的 AR 靶基因表达上调。
关键的时刻来了:这种药物能恢复肿瘤对恩杂鲁胺的敏感性吗?
单独使用恩杂鲁胺对 CRPC-NE 类器官几乎无效,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当恩杂鲁胺与 NSD2i 联用时,奇迹发生了。在小鼠 NPPO-1NE、NPPO-2 以及人类 MSKPCa10 类器官中,这种组合疗法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
为了在更接近真实生理环境的条件下验证这一疗法,研究人员进行了异种移植 (Xenograft) 实验。结果显示,单独使用 NSD2i 虽然能略微抑制肿瘤生长,但效果有限。然而,NSD2i 与恩杂鲁胺的联合治疗,导致了肿瘤生长的强力抑制。在人类 CRPC 类器官 WCM1262、MSKPCa10 和 MSKPCa14 的移植瘤中,联合治疗组的肿瘤体积显著小于对照组和单药组。
组织学分析更是令人振奋:联合治疗组的肿瘤组织出现了大面积的坏死和纤维化,神经内分泌标记物(如 CHGA、SYP、CD56)的表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腺癌特征的恢复。免疫荧光染色显示,Ki67(增殖标记)大幅下降,而 Cleaved Caspase 3(凋亡标记)显著上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 MSKPCa2 这种虽然表达 AR 但对去势治疗有一定抵抗的 CRPC-AR 亚型,NSD2i 甚至在单药治疗下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抑制效果,导致肿瘤体积缩小并诱导凋亡。这提示 NSD2 在维持去势抵抗性方面可能具有超越谱系可塑性的更广泛作用。协同效应分析 (SynergyFinder) 给出的 Bliss 评分进一步量化了这种效果。在多个类器官系中,NSD2i 与恩杂鲁胺的组合均获得了极高的协同评分 (>10),证明二者联手产生了“1+1>2”的效果。相比之下,EZH2 抑制剂与恩杂鲁胺的组合则表现出负的协同评分,暗示了拮抗作用。这一对比有力地支持了针对 NSD2(而非 EZH2)进行靶向治疗的合理性。
重新定义癌症治疗的边界
这项发表在 Nature 上的研究,不仅是前列腺癌治疗领域的一个里程碑,更对我们理解癌症的本质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它证实了表观遗传的可逆性是治疗耐药性癌症的软肋。过去的治疗往往着眼于“杀死”癌细胞,而这项研究展示了“教育”癌细胞的可能性。通过重塑表观遗传景观,我们可以迫使那些已经“黑化”的神经内分泌癌细胞,退回到对常规疗法敏感的腺癌状态。这是一种“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的策略。
其次,它揭示了AR 抑制剂的双刃剑效应。研究中提到,对非神经内分泌类器官使用恩杂鲁胺处理,会导致 NSD2 和 H3K36me2 的上调。这暗示了临床上使用的 AR 抑制剂,在抑制肿瘤生长的同时,可能也在无意中为肿瘤的谱系可塑性创造了“许可”环境 (Permissive State)。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患者在长期接受 AR 抑制剂治疗后会发展出神经内分泌表型。联合使用 NSD2i,或许能阻断这一逃逸路径。
此外,NSD2 的角色可能远不止于此。在 MSKPCa2 这种 CRPC-AR 模型中,NSD2 的缺失也能恢复药物敏感性,甚至直接诱导凋亡。这说明 NSD2 可能通过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直接影响 AR 的转录活性,或者在维持去势抵抗性中扮演着更通用的角色。
最后,这项研究的数据质量和深度令人折服。从 20 多只小鼠模型的建立,到单细胞多组学 (Multiome ATAC+RNA) 的精细解析,再到合成新药并在多种人源化模型中验证,每一个环节都提供了坚实的证据链。例如,在药物筛选中,研究人员不仅看细胞活力,还检测了 caspase 3/7 的活性来确认凋亡;在体内实验中,不仅测量了肿瘤体积,还通过免疫组化确认了组蛋白修饰的改变 (On-target effect)。
对于未来的癌症治疗而言,这或许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不再仅仅根据肿瘤的“长相”(组织学)或“突变”(基因组学)来用药,还要看它的“妆容”(表观遗传学)。NSD2 作为一个曾经被忽视的靶点,如今站在了聚光灯下。它不仅是前列腺癌谱系可塑性的守护者,也可能是我们攻克实体瘤耐药性的一把新钥匙。当我们将目光从基因序列本身移开,投向那些修饰基因的“笔墨”时,或许会发现,癌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战胜。
Li JJ, Vasciaveo A, Karagiannis D, Sun Z, Gretarsson KH, Chen X, Ouerfelli O, Socciarelli F, Frankenstein Z, Dong H, Zou M, Yuan W, Yang G, Aizenman GM, Pannellini T, Xu X, Beltran H, Chen Y, Gardner K, Robinson BD, de Bono J, Gozani O, Abate-Shen C, Rubin MA, Loda M, Sawyers CL, Califano A, Lu C, Shen MM. NSD2 targeting reverses plasticity and drug resistance in prostate cancer. Nature. 2025 Nov 26. doi: 10.1038/s41586-025-09727-z.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1299174.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