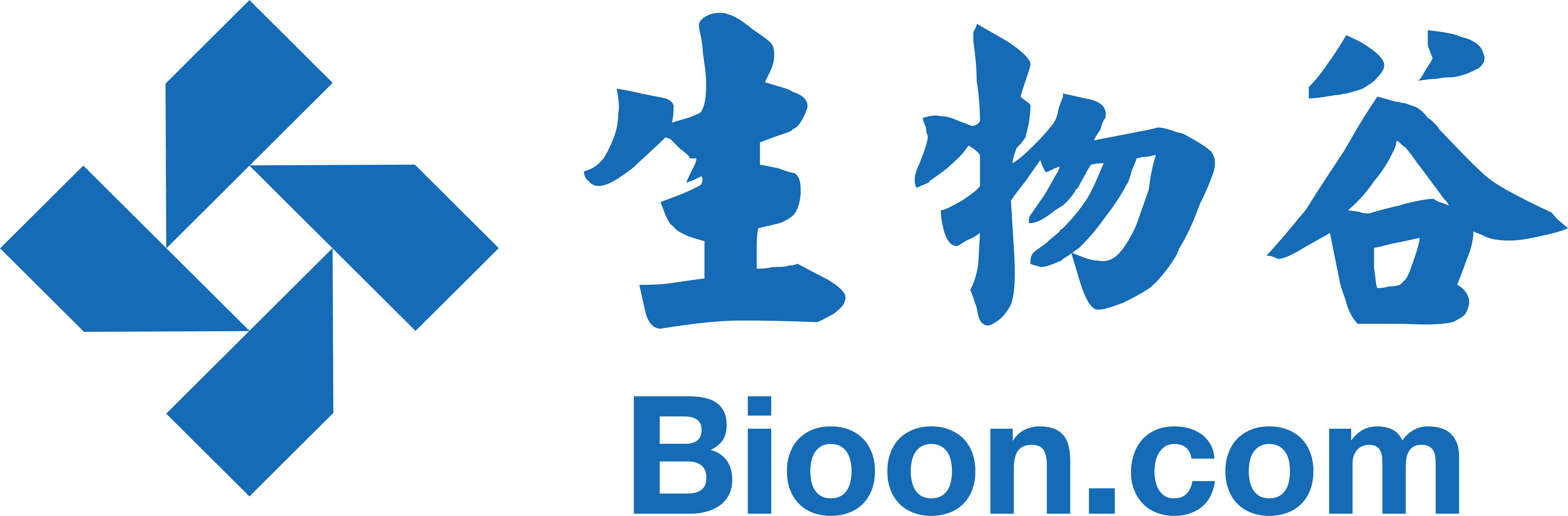STTT:于金明院士团队深度解析放疗与免疫治疗的发展前景
来源:奇点糕 2022-09-01 09:36
给免疫治疗“找个理想的伴儿”,用联合治疗破解当前制约免疫治疗的瓶颈,可能是最近几年里许多科学家和医生的头等大事了。正在进行中的免疫治疗临床研究,就有八成在做联合治疗[1]。
给免疫治疗“找个理想的伴儿”,用联合治疗破解当前制约免疫治疗的瓶颈,可能是最近几年里许多科学家和医生的头等大事了。正在进行中的免疫治疗临床研究,就有八成在做联合治疗[1]。
作为传统的癌症局部治疗手段,放疗就在免疫联合治疗临床研究中屡屡出场,因为学界已经逐渐意识到,放疗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局部控制病灶,它的免疫调节效应也非常值得利用。
尤其是在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同步放化疗后再使用免疫巩固治疗的“PACIFIC模式”大获成功,更让放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备受期待。打破制约免疫治疗的枷锁,让放疗老树开新花,具体应该向哪些方向进军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教授团队,近期就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期刊专门发文,畅谈了新时代放疗+免疫治疗模式(iRT)的发展前景。国内放疗领域的大咖出手,必然不同凡响[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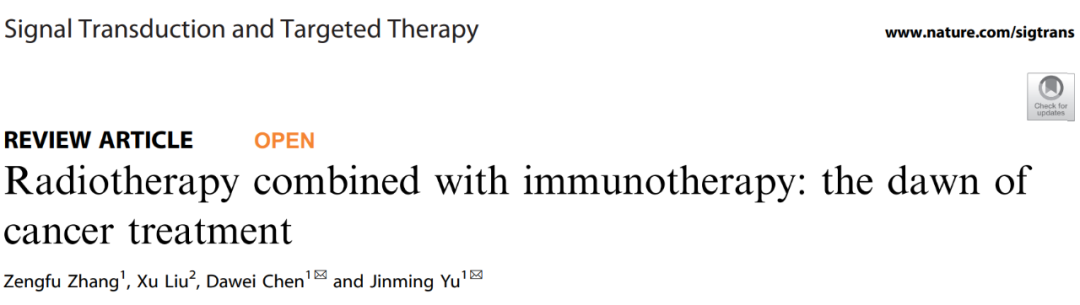
论文首页截图
早在1953年,就有人发现了放疗的“远端效应”(abscopal effect),即局部放疗可能使远处未被照射的病灶消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就是放疗免疫调节效应的表现,2012年一篇登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3]。
而从临床前研究来看,放疗几乎能影响免疫治疗的整个过程,从免疫细胞的致敏和激活,到癌细胞抗原释放和被提呈,释放促炎性细胞因子,调节微环境中的其它细胞……所以在2005年,就有人提出了联合放疗+免疫治疗的iRT模式[4]。
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后,今天的放疗相比几十年前更是强大得多,比如用于部分早期可手术的NSCLC患者时,精准放疗的长期疗效完全能匹敌手术[5]。放疗自身越是精准高效,就能越好地配合免疫治疗。
所以在PACIFIC研究之前,已经有学者尝试过iRT的联合治疗模式,而PACIFIC研究的成功更是让学界“脑洞大开”,比如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张玉蛟教授,就提出了I-SABR的创新iRT模式[6],各种临床研究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
不过于金明院士团队指出,其实在作用机制上,放疗对免疫治疗的影响也明显是一把“双刃剑”,需要综合考量放疗对癌细胞、免疫细胞以及微环境中各种间质细胞的影响,才能做好真正精准的iRT。
放疗对癌细胞的影响
放疗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杀伤癌细胞,即高能放射线直接诱导DNA断裂或诱导癌细胞内活性氧的产生,而这两种途径都会进一步影响癌细胞和免疫细胞的生物学行为,从而改变肿瘤微环境,进而影响到免疫治疗。
比如在发生DNA断裂后,癌细胞就需要激活DNA损伤修复(DDR)机制,但各种致癌基因突变往往会导致DDR异常,继续增加癌细胞基因组的不稳定性,从而激活cGAS-STING信号通路,免疫系统就很可能收到警报而被激活。
放疗在癌细胞内诱导生成的活性氧,也可以通过类似的途径激活STING通路,诱导I型干扰素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应答,此外含有DNA的癌细胞外泌体也可能转运到树突状细胞,这些都是放疗激活系统性抗肿瘤免疫应答的潜在机制。
放疗对肿瘤间质细胞的影响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是大多数肿瘤间质内的主要成分,它们并不容易被放疗直接杀死,但也会出现DNA损伤和下游信号通路的变化。有研究显示,放疗会一定程度上限制CAFs的促癌作用,但同时被放疗照射后的CAFs又有免疫抑制作用,因此放疗对间质细胞的影响还需要深入评估。
放疗对各类免疫细胞的影响
之所以会说放疗对免疫治疗的影响是“双刃剑”,就与放疗对免疫细胞的影响有关,除了直接杀伤对免疫治疗至关重要的细胞毒性T细胞、B细胞外,放疗还对另外几类免疫细胞有不小的影响。
1)免疫调节性T细胞(Treg)
大量研究显示,放疗后肿瘤部位的Treg数量会明显增多,表型和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导致微环境进入抑制状态,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被放疗激活的STAT3通路和表达明显上调的TGF-β。
2)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ANs)/巨噬细胞(TAMs)
放疗对TANs的作用相对而言还不算明确,N1型TANs可能被诱导出抗癌效应,诱导癌细胞的凋亡,并激活细胞毒性T细胞,但N2型TANs的表现却恰好相反,它们可能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和NK细胞的抗肿瘤应答。
而TAMs也能分为M1和M2两型,放疗的影响同样是正反两面,M1型TAMs可以通过吞噬作用消灭癌细胞,但M2型TAMs则可能与Treg联手抑制免疫应答,此外TAMs向M1或M2型的极化,也可能受到放疗的影响。
3)髓系来源的免疫抑制细胞(MDSCs)
作为免疫微环境中的主要免疫抑制性细胞,MDSCs一般会在放疗照射肿瘤部位后数量明显增加,并被募集到肿瘤部位,导致明显的免疫抑制效应,而cGAS/STING通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树突状细胞
树突状细胞可以被放疗直接激活,此外还有多种间接激活途径,比如放疗杀死癌细胞后,会释放大量抗原及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DAMPs),这些都是树突状细胞的“兴奋剂”,但一小部分树突状细胞也可能参与了放疗后的免疫抑制。
重新看待放疗的“远端效应”
说了这么多放疗对全身免疫状态产生的影响,但实际在临床中观察到的放疗“远端效应”却并不多,对此于金明院士团队认为,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问世前,单纯由放疗带来的免疫应答改变,大多数时候不足以导致病灶消退,但在iRT联合治疗时代,看待远端效应也应该有全新的视角。
远端效应可以分为宏观、分子和基因三个层面来看,虽然宏观层面肿瘤不一定缩小,但放疗几乎必然会导致分子和基因层面的改变,比如上面的放疗杀死癌细胞、释放抗原及DAMPs,这些发生在照射局部的改变,都是远端效应激活全身免疫应答的关键,而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三种层面上的“远端效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根治性、高剂量放疗不同,不以杀死癌细胞为目标的低剂量放疗,可能更有利于调节免疫微环境,减少高剂量放疗导致的免疫抑制,从而有效配合免疫治疗,“低剂量放疗就像是打开了城门,把免疫细胞、效应分子这些援兵放进来”,而这可能主要与低剂量放疗诱导的癌细胞DNA损伤有关。
于金明院士团队借用了国外学者的说法,将低剂量放疗这种独特的效应命名为“放疗远端效应”(Radscopal effect,区别于传统的远端效应)[7],也有初步临床研究证实了放疗远端效应的用处[8]。还有临床研究尝试高剂量+低剂量放疗联合使用,从而全面发挥放疗的远端效应,有效控制了部分晚期患者的转移灶[9]。
寻找提示iRT疗效的生物标志物
虽说免疫+放疗的iRT模式前景广阔,但与现有免疫治疗类似,也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治疗中获益,因此理想的使用策略就是通过生物标志物,优先筛选出潜在的获益人群,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TMB)这些标志物,估计也不能直接照搬到iRT当中,所以还是需要从机制出发来寻找适用的新型标志物。
例如属于DAMPs之一的钙网蛋白(calreticulin),就是放疗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的关键分子,它的出现可能就提示放疗有效调节了免疫应答;于金明院士团队还提到了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计数(ALC),有研究显示治疗前后的ALC水平均与放疗远端效应有关,可以用于疗效预测和预后评估。
来自临床实践的iRT应用模式初探
免疫治疗和放疗的联合要想实现1+1>2,当然也不是易如反掌,免疫治疗的药物类型、免疫与放疗的先后顺序、放疗的剂量、分割及照射部位,都可能影响联合治疗的效果,有许多研究在探索最优使用模式,从而将协同增效最大化。
影响iRT疗效和安全性的因素确实非常多
1)放疗的剂量及分割
放疗对免疫应答的调节,在一定范围内也有“剂量依赖性”,但≥15Gy的高剂量放疗又可能导致免疫抑制,因此可以考虑大分割放疗模式,已有在晚期NSCLC中开展的早期临床研究显示,高剂量大分割SBRT(50Gy/4次)联合PD-1抑制剂在多个疗效终点上,都优于传统放疗(45Gy/15次)+PD-1抑制剂[10]。
2)放疗的照射部位
研究显示,放疗照射位于不同部位的转移病灶,对全身免疫应答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理想的当然是把所有病灶都照射一遍,但考虑到患者的耐受性,可能应优先考虑低剂量放疗,还应注意不同癌症对放疗的敏感性问题。
3)放疗的使用时机
目前学界争论最大的话题,就是免疫治疗和放疗应该是“序贯使用”还是“同步使用”,虽然PACIFIC研究的免疫巩固模式,也就是先放疗(放化疗)后用免疫大获成功,但从一些真实世界研究来看,序贯治疗患者的肺炎发生率也还是比较高的[11],另外在放疗后开始使用免疫治疗的时机,可能也与疗效有关。
而以KEYNOTE-799为代表的一些临床早期研究则显示,免疫治疗与放疗同步使用有望进一步提高疗效,安全性也与序贯治疗大体相当,这也是近年来大规模临床研究的重点探索方向。于金明院士团队还介绍,以纳米材料作为免疫调节剂或放疗增敏剂,还有望进一步提升iRT的疗效。
4)免疫疗法的选择
有回顾性研究显示,PD-1/L1抑制剂联合放疗,用于NSCLC患者的疗效明显优于CTLA-4抑制剂+放疗[12],但结论仍有待前瞻性数据证实,还不能说PD-1/L1抑制剂是更合适放疗的搭档。
正在进行的CheckMate-73L研究,则将评估PD-1+CTLA-4双免疫方案与PD-1抑制剂单药,在局部晚期NSCLC中作为免疫巩固治疗的价值,不过从II期研究来看,双免疫方案的毒性及其导致的停药是不容忽视的[13]。
5)iRT毒性问题
放疗可能导致肺损伤、心脏疾病和肝损伤,而免疫治疗也有免疫相关肺炎、结肠炎、肝炎等典型副作用,二者联合使用的安全性也是临床焦点,例如NSCLC临床研究中比较多见的放射性肺炎问题,不过现有数据显示,放射性肺炎大多并不严重,需医疗干预乃至危及生命的3-4级肺炎比较少见,风险还是小于治疗获益的。
结语
照射多病灶的免疫调节效应、低剂量放疗专属的“远端效应”,以及放疗激活的全身免疫应答,都让iRT联合治疗模式颇受期待,但在iRT被临床常规应用之前,还需要跨越一系列的难关和挑战,相信未来的临床研究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参考文献:
1.Upadhaya S, Neftelinov S T, Hodge J, et 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PD1/PDL1 inhibitor clinical trial landscape[J].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2022, 21: 482-483.
2.Zhang Z, Liu X, Chen D, et al. Radiotherapy combined with immunotherapy: the dawn of cancer treatment[J].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2022, 7: 258.
3.Postow M A, Callahan M K, Barker C A, et al. Immunologic correlates of the abscopal effect in a patient with melanoma[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2, 366(10): 925-931.
4.Demaria S, Bhardwaj N, McBride W H, et al. Combining radiotherapy and immunotherapy: a revived partnershi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 Biology* Physics, 2005, 63(3): 655-666.
5.Chang J Y, Mehran R J, Feng L, et al. 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for operable stage I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revised STARS): long-term results of a single-arm, prospective trial with prespecified comparison to surgery[J]. The Lancet Oncology, 2021, 22(10): 1448-1457.
6.Bernstein M B, Krishnan S, Hodge J W, et al. Immunotherapy and 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ISABR): a curative approach?[J]. 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 2016, 13(8): 516-524.
7.Barsoumian H B, Ramapriyan R, Younes A I, et al. Low-dose radiation treatment enhances systemic antitumor immune responses by overcoming the inhibitory stroma[J]. 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2020, 8(2): e000537.
8.Welsh J W, Tang C, De Groot P, et al. Phase II Trial of Ipilimumab with Stereotactic Radiation Therapy for Metastatic Disease: Outcomes, Toxicities, and Low-Dose Radiation–Related Abscopal ResponsesIpilimumab and SABR for Lung or Liver Metastases[J]. 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 2019, 7(12): 1903-1909.
9.Patel R R, He K, Barsoumian H B, et al. High-dose irradi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non-ablative low-dose radiation to treat metastatic disease after progression on immunotherapy: Results of a phase II trial[J]. Radiotherapy and Oncology, 2021, 162: 60-67.
10.Welsh J, Menon H, Chen D, et al. Pembrolizumab with or without radiation therapy for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J]. 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2020, 8(2): e001001.
11.Jung H A, Noh J M, Sun J M, et al. Real world data of durvalumab consolidation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in stage III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J]. Lung Cancer, 2020, 146: 23-29.
12.Chen D, Menon H, Verma V, et al. Response and outcomes after anti-CTLA4 versus anti-PD1 combined with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for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wo single-institution prospective trials[J]. 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2020, 8(1): e000492.
13.Yan M, Durm G A, Mamdani H, et al. Consolidation nivolumab/ipilimumab versus nivolumab following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stage III NSCLC: A planned interim safety analysis from the BTCRC LUN 16-081 trial[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0, 38(Suppl_15): 9010.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