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细胞的“罗生门”——为何同一种病毒,偏偏只感染“你”?
来源:生物探索 2025-11-20 13:42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巧妙的方法,成功地“回溯时光”,窥见了那些注定要被感染的细胞在“出事”之前的真实状态。
想象一个拥挤的房间,有人打了个喷嚏,感冒病毒瞬间弥漫在空气中。几天后,有些人安然无恙,有些人却开始流涕、咳嗽。我们通常将此归因于个体免疫力的差异。但如果我们将场景切换到微观世界,进入由成千上万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细胞组成的组织中,一个更为根本且令人困惑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当病毒大军压境时,为何有些细胞会被感染,而它们旁边遗传背景一模一样的“邻居”却能幸免于难?
这并非偶然。长期以来,研究人员观察到,即使在最均一的细胞培养体系中,病毒感染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这种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生命法则?是病毒的随机碰撞,还是细胞本身早已“命中注定”?
解答这个问题,远比想象中困难。最大的障碍在于,病毒一旦进入细胞,就会迅速“篡改”宿主的生命程序,关闭其正常的转录和翻译,使其沦为病毒复制的工厂。当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被感染细胞的基因表达来寻找其易感的原因时,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被病毒“魔改”后的状态,而非它被感染前的“素颜”。这就像一场凶案,当我们赶到现场时,所有线索都已被凶手破坏,无法追溯最初的真相。
然而,11月14日,《Cell》的研究报道“Single-cell susceptibility to viral infection is driven by variable cell states”,为我们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一把前所未有的钥匙。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巧妙的方法,成功地“回溯时光”,窥见了那些注定要被感染的细胞在“出事”之前的真实状态。他们的发现不仅深刻揭示了病毒感染的内在逻辑,也为我们理解疾病的个体差异和开发新的抗病毒策略指明了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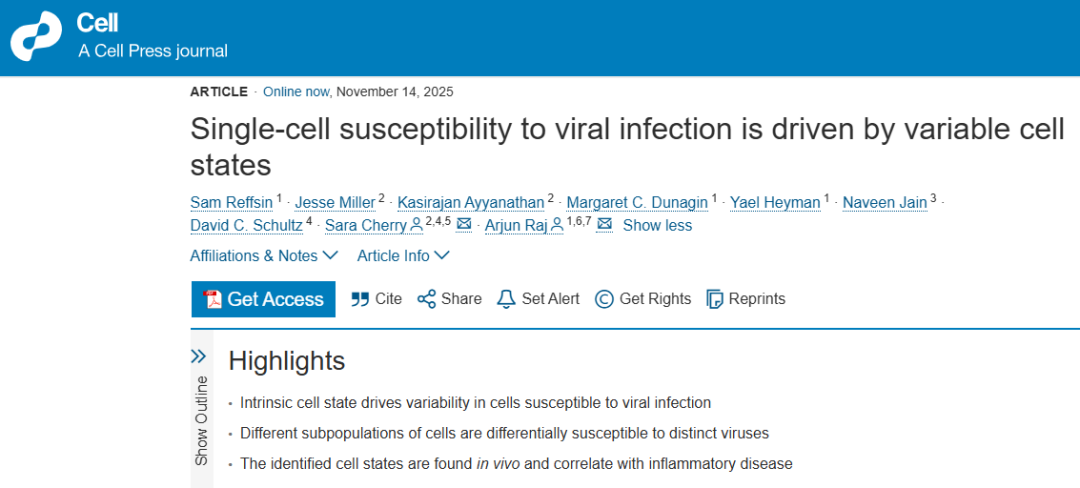
为细胞命运按下“倒带”键:一种巧妙的追踪溯源技术
要破解“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是细胞状态导致了感染,还是感染改变了细胞状态,关键在于拥有一个能在感染发生之前就洞悉细胞内在特性的“预言家”。传统方法做不到这一点,但该研究团队另辟蹊径,利用一种名为“Rewind”的单细胞克隆追踪(single-cell clone tracing)技术,实现了对细胞命运的“时空穿越”。
这个技术的精髓可以这样理解:
首先,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条形码文库”(barcode library),这些DNA条形码通过慢病毒载体被随机整合到单个细胞的基因组中。每个细胞及其后代(即一个克隆)都将带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可遗传的“身份证”。
接下来,他们让这些带上了“身份证”的细胞进行分裂增殖。当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时,它们就成了一对拥有相同遗传背景和“身份证”的“同卵双胞胎”。研究人员巧妙地将这些细胞“双胞胎”兵分两路:
一路(存档组):立即进行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这相当于为每个细胞克隆在某个时间点拍摄了一张详尽的“分子快照”,记录下它此刻的基因表达状态,也就是它的“细胞状态”(cell state)。
另一路(实验组):暴露在新冠病毒(SARS-CoV-2)的环境中。一段时间后,利用荧光标记病毒RNA的方法,将被感染的细胞和未被感染的细胞分选开来。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研究人员分别提取实验组中“被感染”和“未被感染”细胞群体的DNA,读取它们的“身份证”条形码。通过将这些条形码与“存档组”的“分子快照”进行匹配,他们就能精确地回答这个核心问题:那些最终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它们在被感染前的“双胞胎兄弟”究竟是什么模样?
这种方法如同拥有了一台细胞命运的录像机,它先录下每个细胞的初始状态,然后快进播放它们经历病毒感染的过程,最后再“倒带”回去,仔细审视那些“中招”细胞的原始录像。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成功绕过了病毒对细胞的干扰,直击了决定易感性的内在本质。
“易感者”的画像:TIG1高表达状态的浮现
利用这套强大的“Rewind”系统,研究人员以人肺腺癌细胞系Calu-3作为模型,这是一个研究呼吸道病毒的经典模型,因为它能很好地模拟人类呼吸道上皮细胞的特性。他们发现,在感染新冠病毒24小时和48小时后,那些被感染细胞的“身份证”,在“存档组”的细胞图谱中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显著地富集在两个特定的细胞亚群中。
其中一个亚群是快速增殖的细胞,这符合我们的普遍认知,即活跃的细胞可能更容易被病毒利用。但更有趣的是另一个亚群,它被一个名为TIG1(Tazarotene-induced gene 1)的基因高表达所标记。这个细胞亚群,研究人员称之为“TIG1-high”状态,似乎是新冠病毒的“理想猎物”。
深入分析发现,“TIG1-high”不仅仅是单个基因的升高,而是一整个基因表达程序的协同激活,这个程序与维甲酸信号通路(retinoic acid signaling)密切相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表达大量干扰素刺激基因(Interferon-stimulated genes, ISGs)的细胞亚群,也就是处于“JAK/STAT”信号激活状态的细胞,则表现出天然的抵抗力,几乎没有一个被感染的细胞克隆来源于这个亚群。这表明,细胞内在的、自发的基因表达模式,已经预先决定了它们在病毒面前的命运:一些细胞开启了“欢迎模式”(如TIG1-high),而另一些则启动了“防御模式”(如JAK/STAT激活)。
为了验证这些基因是否不仅仅是“旁观者”的标记,而是决定命运的“操盘手”,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基因敲除实验。他们利用CRISPR-Cas9技术,系统性地敲除了在“TIG1-high”状态下高表达的多个基因,包括`AXL`、`TSPAN8`、`MUC20`以及`TIG1`本身。结果非常清晰:敲除这些基因后,细胞对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均出现了显著下降。这有力地证明了,“TIG1-high”状态下的这些基因,共同构建了一个有利于病毒入侵和复制的“微环境”。
超越ACE2:病毒受体并非易感性的唯一“通行证”
谈到新冠病毒感染,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它的“钥匙”——ACE2受体(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理论上,细胞表面的ACE2蛋白越多,病毒进入细胞的机会就越大。那么,细胞的易感性差异,是否仅仅是ACE2表达水平的差异呢?
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结果却发现故事远比这复杂。
通过单细胞测序和RNA原位杂交(smFISH)技术,他们发现在Calu-3细胞群体中,能够检测到ACE2 mRNA的细胞非常稀少。即使转向检测ACE2蛋白,他们发现虽然有大约9%的细胞表达高水平的ACE2蛋白,但实际被感染的细胞比例要低得多(例如,24小时后仅为1.5%)。这说明,高表达ACE2是细胞被感染的必要条件,但远非充分条件。
真正的“天选之子”,那些最易感的细胞,究竟是谁?
研究人员通过免疫荧光和smFISH联用的方法,同时检测了单个细胞中的ACE2蛋白和TIG1 mRNA。数据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现象:ACE2蛋白的高表达和TIG1的高表达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一个细胞同时为ACE2-high和TIG1-high的几率,是随机情况下的33.16倍。
然而,即便如此,也只有约28.7%的ACE2-high细胞同时是TIG1-high。这意味着,在所有手持“入场券”(ACE2-high)的细胞中,只有一小部分同时激活了“TIG1-high”这个“VIP通道”,它们才是病毒最优先攻击的目标。相比之下,另一个黏蛋白基因MUC5AC虽然也与ACE2表达有一定相关性,但其关联强度(几率为2.63倍)远低于TIG1。
这一发现颠覆了以往将病毒易感性主要归因于受体表达水平的简单模型。它揭示了一个更为精细的调控层次:病毒的易感性由一个多基因、多维度的“细胞状态”决定,而不仅仅是单个受体分子的有无或多少。ACE2可能只是打开了第一道门,而“TIG1-high”状态则为病毒铺平了后续入侵和复制的所有道路。
揭秘“易感状态”的调控网络:谁是幕后推手?
既然“TIG1-high”是一个由多个基因构成的复杂状态,那么这些基因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调控关系?它们是“一盘散沙”,还是一个组织有序的“犯罪团伙”?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运用了伪时间分析(pseudotime analysis)的计算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根据单细胞基因表达谱的渐进式变化,推断出细胞状态演化的“轨迹”和“时间轴”。分析结果显示,从普通的增殖细胞分化到易感的“TIG1-high”状态,存在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这条路径上,不同基因的表达呈现出鲜明的时序性:基因`AXL`和`TSPAN8`的表达在轨迹的早期就已升高,紧随其后的是`TIG1`,而`CEACAM1`、`MUC20`和`CTSS`等基因则在轨迹的末端才达到峰值。这一时序性暗示了一个潜在的调控级联反应:早期的基因(如`AXL`、`TSPAN8`)可能作为“主谋”,启动并调控了下游基因(如`TIG1`、`MUC20`)的表达,从而共同塑造了整个“易感状态”。
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上的推测。研究人员再次通过基因敲除实验验证了这个假说。他们发现:
敲除上游的`AXL`或`TSPAN8`,不仅自身表达消失,下游的`TIG1`和`MUC20`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下降。例如,敲除`AXL`后,表达高水平TIG1的细胞比例从9.9%骤降至1.0%,高水平MUC20的细胞比例也从10.0%降至2.0%。
敲除处于中间位置的`TIG1`,下游的`MUC20`表达也随之降低,但对更上游的`AXL`或`TSPAN8`没有影响。
敲除最下游的`CEACAM1`或`CTSS`,则几乎不影响其他任何“易感基因”的表达。
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证据,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调控网络。`AXL`和`TSPAN8`如同两个“开关”,一旦被按下,就会启动一个导向“TIG1-high”状态的程序化进程。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干预这些上游的“主谋”基因,来瓦解整个“易感状态”,从而达到广谱预防病毒感染的目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某个下游的执行者。
从培养皿到真实世界:这种“易感细胞”在人体内存在吗?
这个在Calu-3细胞中发现的“TIG1-high”易感状态,是否仅仅是培养皿中的“特例”,还是在真实的人类肺脏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分析了公开的人类肺脏单细胞测序数据库。他们首先在复杂的肺组织中识别出了各种上皮细胞类型,包括基底细胞(basal cells)、肺泡I型和II型细胞(AT1/AT2 cells)、棒状细胞(club cells)以及纤毛细胞(ciliated cells)。
结果令人振奋:“TIG1-high”基因特征谱在人体肺脏中确实存在,并且主要富集在棒状细胞和纤毛细胞中。这两种细胞类型,恰好也是已知的新冠病毒在肺部的主要攻击目标。这表明,实验室中的发现与体内的真实情况高度吻合。
更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这种“易感状态”与临床疾病的潜在关联。研究人员比较了健康人与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PF)患者的肺组织样本。IPF是一种严重的、病因不明的慢性肺病,其患者感染新冠后往往预后更差。分析发现,在IPF患者的肺部,不仅纤毛细胞的比例增加,表达高水平`TIG1`和`MUC20`的棒状细胞和纤毛细胞的频率也显著高于健康人。
此外,他们还发现,在有吸烟史的健康人群中,其肺部表达高水平`TIG1`和`MUC20`的细胞比例也显著高于非吸烟者。
这些发现如同一座桥梁,将微观的“细胞状态”与宏观的临床风险因素(如肺部基础疾病、吸烟)紧密联系起来。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为何某些人群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或发展成重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的肺部由于疾病或环境因素的影响,已经预先存在了更多处于“TIG1-high”易感状态的细胞,为病毒的入侵和肆虐准备了“温床”。
病毒的“择偶标准”:流感病毒为何“情有独钟”另一类细胞?
“TIG1-high”状态是所有呼吸道病毒的“万能钥匙”吗?还是说,不同的病毒有其独特的“品味”和“择偶标准”?
为了探索病毒的特异性,研究团队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甲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 virus)。他们重复了与新冠病毒类似的“Rewind”实验,追踪那些容易被流感病毒感染的细胞在感染前的状态。
结果再次带来了惊喜。流感病毒感染的细胞克隆,其条形码并未富集在“TIG1-high”细胞亚群中。相反,它们显著地集中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细胞亚群里。这个亚群的特征是高表达角蛋白8和18(`KRT8`, `KRT18`)以及`SPP1`等基因,呈现出一种“过渡性干细胞”(transitional stem cell)的状态。
这个发现极具启发性。它表明,即便在同一个细胞群体(Calu-3)中,也并存着对不同病毒特异的“易感状态”。新冠病毒偏爱“TIG1-high”状态的细胞,而流感病毒则青睐“KRT8-high”的过渡态细胞。这就像两位不同的猎人,进入同一片森林,却各自追踪着不同的猎物。
这种病毒特异性,也体现在不同新冠病毒变种上。研究人员比较了原始毒株(WA1)和奥密克戎变种(BA.1)对细胞的感染偏好。他们发现,尽管“TIG1-high”状态的细胞对两种毒株都表现出更高的易感性,但这种偏好性在感染原始毒株时更为显著。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变种的致病性会有所差异,病毒的进化,可能也伴随着其对宿主细胞“易感状态”偏好的微调。
超越“是否感染”,走向“为何易感”的深层思考
这项发表于《Cell》的研究,通过其巧妙的实验设计和翔实的数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病毒与宿主细胞互作的全新图景。它告诉我们,决定一个细胞是否被病毒感染的,远不止细胞表面是否有病毒受体那么简单。在遗传背景之下,存在一个由内在基因表达程序定义的、动态变化的“细胞状态”维度。正是这些瞬息万变的细胞状态,构成了病毒感染的“微观战场”,决定了谁是“易感者”,谁是“抵抗者”。
这项工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为理解病毒嗜性(viral tropism)提供了新的视角。病毒为何只感染特定类型的组织和细胞?传统的答案是受体分布。而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受体阳性的细胞群体中,病毒的攻击目标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它们瞄准的是那些处于特定“易感状态”的细胞亚群。
其次,它为解释疾病的个体差异提供了分子层面的依据。为何同样暴露于病毒,不同人的病情轻重会有天壤之别?除了宏观的免疫系统差异,微观层面细胞“易感状态”的基线水平可能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一个肺部“TIG1-high”细胞比例更高的人,可能在感染初期就为病毒提供了更多的“滩头阵地”。
最后,它为开发新的抗病毒策略开辟了道路。传统的抗病毒药物主要靶向病毒本身(如抑制其复制酶或蛋白酶),但这容易导致病毒耐药。这项研究提示我们,或许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不直接攻击病毒,而是通过药物干预宿主,将细胞从“易感状态”调控到“抵抗状态”。例如,开发能够抑制`AXL`或`TSPAN8`等上游调控因子的药物,就有可能关闭整个“TIG1-high”程序,从而“拒病毒于千里之外”。
生命之美,在于其复杂与精准。从一个个细胞的命运抉择,到一个个体的健康与疾病,再到一场全球大流行的演变,背后都遵循着深刻的生物学逻辑。这项研究,正是对这一逻辑的精彩解码。它让我们明白,面对病毒的侵袭,细胞并非无辜的“傻白甜”,它们的内在状态,早已在冥冥之中写下了各自不同的剧本。而读懂这些剧本,正是我们战胜疾病的希望所在。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