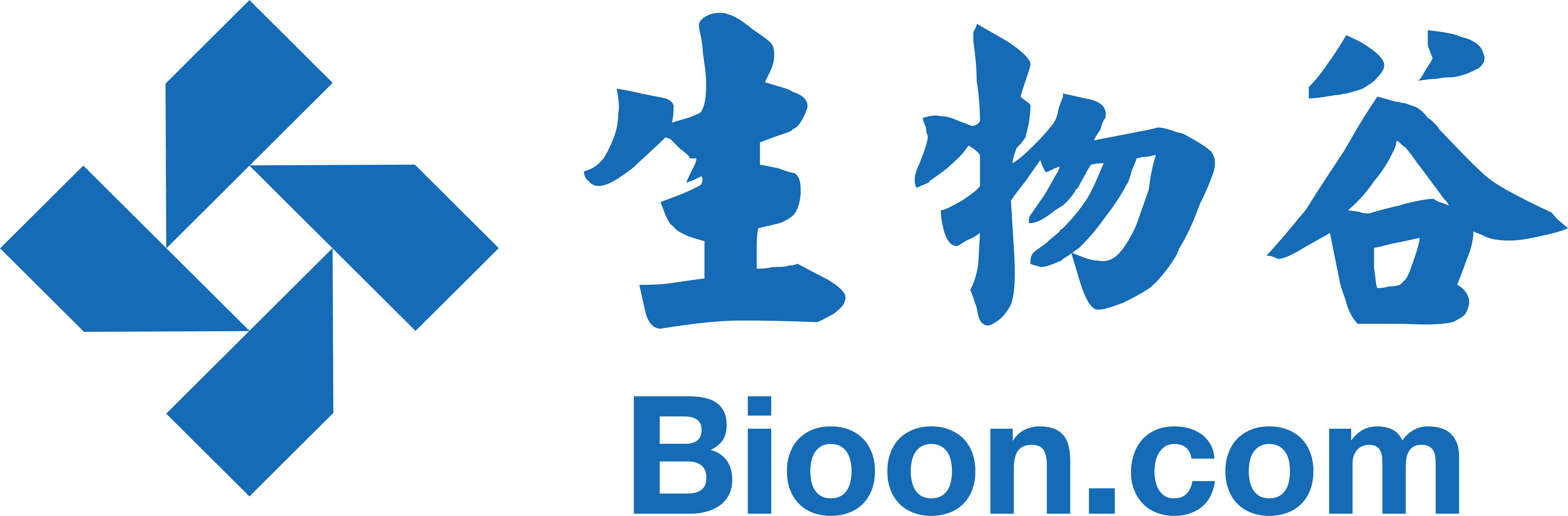Nature Genetics:告别“批量”模糊——首个大规模单细胞研究,解码胶质母细胞瘤纵向演变的“个体差异”与“普遍规律”
来源:生物探索 2025-05-14 14:00
这项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它提示我们,GBM复发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过程。理解每个患者肿瘤独特的演变轨迹以及驱动这一轨迹的关键因素,是实现精准治疗的关键。
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GBM),是脑肿瘤中最凶险、最难缠的一种,手术、放疗、化疗轮番上阵,也常常难以彻底清除。许多患者在短暂缓解后,肿瘤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而且复发时的肿瘤似乎变得更加狡猾、更难对付。为什么GBM如此难以驯服?它在治疗压力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复发的肿瘤还是原来的“恶魔”吗?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就像试图理解一个复杂城市的人口变迁,只能通过“批量”数据(bulk data),看到肿瘤作为一个整体的总貌。但这就像只知道城市总人口和经济总量,却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种职业、不同社区构成如何变化,以及这些社区是如何相互影响的。GBM内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ecosystem),不仅有疯狂生长的恶性肿瘤细胞,还有各种各样的“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细胞,比如免疫细胞、血管细胞以及被肿瘤劫持的正常脑细胞。这些细胞的种类、比例、状态,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都在动态演变,共同决定了肿瘤的命运。
要真正揭开GBM复发的“变脸术”,我们需要一个更高清的视角,看到“城市”里的每一个“居民”及其变化。得益于单细胞组学技术(single-cell genomics),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做到了。
《Nature Genetics》的研究报道“Deciphering the longitudinal trajectories of glioblastoma ecosystems by integrative single-cell genomics”,汇集了全球顶尖力量,对近60名GBM患者在初发和复发时的肿瘤样本进行了“单细胞”层面的深入分析。这不仅仅是对比两个时间点,更是追踪同一个肿瘤在治疗前后的“纵向演变轨迹”(longitudinal trajectories)。他们在这趟“单细胞”的探索之旅中发现了哪些令人惊叹、甚至有些出乎意料的秘密?GBM复发到底遵循着怎样的“规则”?那些躲过治疗的“种子”又是如何重塑肿瘤生态系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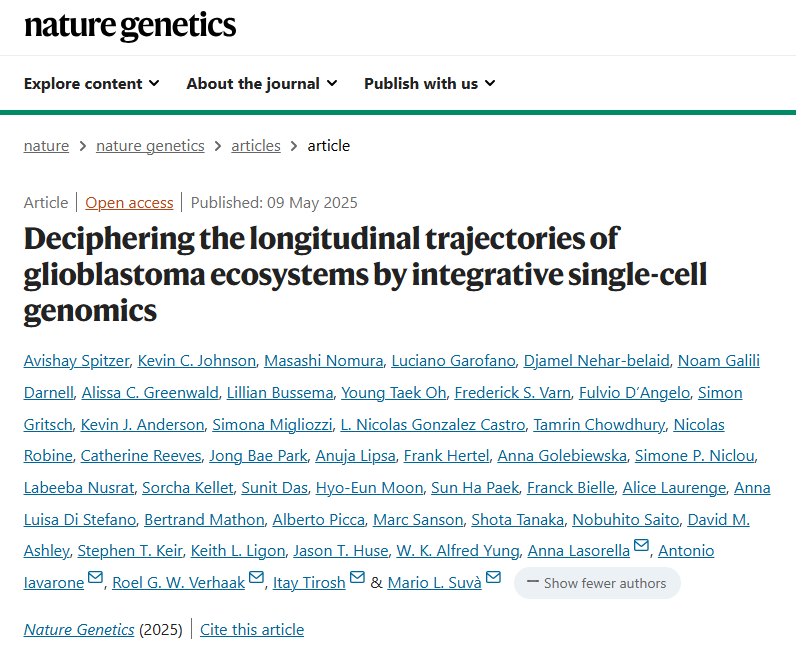
进入“单细胞”时代:解码肿瘤生态系统的秘密
近年来,单细胞组学(single-cell genomics)技术取得了突破,让我们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去“窥探”肿瘤内部的每一个细胞。这项技术能够分别检测肿瘤中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通过单核RNA测序single-nucleus RNA sequencing,snRNA-seq)或基因组变异(通过单细胞DNA测序)。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正是利用了这种强大的工具,深入研究了GBM在接受标准治疗前(初发,Primary,T1)和复发后(复发,Recurrence,T2/T3)的演变轨迹。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GBM CARE(Glioblastoma Cellular Analysis of Resistance and Evolution,胶质母细胞瘤耐药性和演变细胞分析)的大型研究联盟,汇集了来自全球多家顶尖医院的59名GBM患者的肿瘤样本。对于这些患者,他们收集了初发和复发时的配对肿瘤样本,总共分析了121个肿瘤样本,并对其中约43万个细胞的单核RNA进行了测序,同时对肿瘤组织进行了批量DNA测序(WES/WGS)。
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前所未有的规模(59对匹配样本)和多组学整合分析(单细胞转录组 + 批量基因组),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1) 清晰地区分肿瘤中的恶性细胞和非恶性细胞;2) 详细刻画这些细胞在治疗前后的“身份”(细胞类型Cell Type)和“状态”(Malignant Cell State,即恶性细胞的不同转录组亚型);3) 追踪肿瘤生态系统的整体“构成”(Composition)在治疗前后的变化;4) 探索基因组变异对细胞状态演变的影响;5) 最重要的一点,对比初发和复发样本,揭示GBM生态系统的纵向演变轨迹。
复发肿瘤的“新面貌”:恶性细胞退潮,脑神经细胞登场?
通过对这59对匹配的初发和复发GBM样本进行详细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在肿瘤复发时普遍出现的“新面貌”。
其中最一致的变化发生在肿瘤生态系统的构成层面:相比于初发肿瘤,复发肿瘤中的恶性细胞比例显著降低。与此相对应的是,肿瘤微环境中的一些非恶性细胞,尤其是属于“胶质-神经”(glio-neural)类群的细胞,比例显著增加。这些细胞主要包括少突胶质细胞(Oligodendrocyte)、神经元(Neuron)以及星形胶质细胞(Astrocyte,ACs)。具体来说,研究发现,在66%的病例中观察到了这种恶性细胞比例降低和胶质-神经TME细胞比例增加的趋势。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研究人员还分析了一个独立的、已发表的GBM单细胞数据集,结果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复发肿瘤中恶性细胞更少,而少突胶质细胞比例更高。
更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根据肿瘤复发时的细胞构成(恶性细胞比例高低,以及低恶性细胞比例肿瘤中占主导的TME细胞类型)将患者分成了不同的组别。结果显示,那些在复发时表现为“低恶性细胞比例且胶质-神经TME占主导”(LMF-GN)的患者,在接受第二次手术后,生存时间显著长于其他组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19个月,而其他组为8个月,Log-rank检验 P = 0.012)。这提示我们,复发肿瘤的细胞构成可能与患者的预后息息相关,胶质-神经TME的富集或许预示着一个相对“温和”的复发类型。
恶性细胞的“百变状态”:没有统一的“剧本”
除了整体细胞构成的变化,恶性肿瘤细胞本身也具有高度的转录组异质性,表现为不同的“细胞状态”(cell states)。这项研究根据基因表达模式,将恶性细胞划分为了十种主要的状态,包括细胞周期(Cell Cycle)、星形胶质细胞样(AC-like)、间充质样(MES-like)、应激(Stress)、缺氧(Hypoxia)、神经祖细胞样(NPC-like)、少突胶质细胞祖细胞样(OPC-like)、分化神经元样(NEU-like)、胶质祖细胞样(GPC-like)以及纤毛相关状态(Cilia-like)。此外,研究还定义了三种与细胞状态比例无关的、反映肿瘤间异质性的“基线基因表达谱”(Baseline Profiles,BP),分别注释为胶质BP(Glial-BP)、细胞外基质BP(ECM-BP)和神经元BP(Neuronal-BP)。
先前一些基于批量测序的研究曾提出,GBM复发时常常发生从“神经祖细胞样”(proneural)到“间充质样”(MES-like)的转变。然而,这项大型单细胞研究却揭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景象:在整个队列中,研究没有观察到任何一种特定的恶性细胞状态在复发时普遍富集。也就是说,GBM恶性细胞在治疗前后的“状态转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剧本”。
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没有统一的转变趋势,某些恶性细胞状态的存在确实与预后相关。例如,研究发现在复发肿瘤中,如果间充质样/缺氧(MES-like/Hypoxia)状态占主导,患者在第二次手术后的生存时间显著更短(中位生存时间为5个月,而其他恶性细胞状态占主导的患者为10.3个月,Log-rank检验 P = 0.00086)。这再次印证了肿瘤细胞状态对患者预后的重要影响。
个体轨迹的“迷宫”:千变万化的复发路径
如果从单个患者的角度来看,GBM的复发轨迹则更加“捉摸不透”。尽管群体层面显示了一些平均趋势(如恶性细胞减少),但当研究人员对比每一对匹配的初发和复发样本时,发现肿瘤的演变轨迹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
数据显示,大多数样本对在细胞构成组别上发生了变化,高达68%的样本对从初发时的某种构成组别转变为复发时的另一种。同样,64%的样本对在主要的恶性细胞状态组别上发生了转变,56%在基线基因表达谱组别上发生了转变。研究甚至观察到了截然相反的演变轨迹,例如某个患者复发时AC-like细胞增加而GPC-like细胞减少,而另一个患者则恰好相反。
这种巨大的个体差异使得GBM的复发轨迹如同一个“迷宫”。尽管如此,这项研究发现,匹配的初发-复发样本对之间的转录组相似度仍然显著高于随机配对的样本。这意味着虽然路径多样,但同一患者的肿瘤在演变过程中保留了某种程度的“身份连续性”,它们之间的相似度仍然比随机选取的两个肿瘤更高。这提示我们,复发并非完全随机,而是初发肿瘤固有特征与治疗及微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拨开迷雾:谁在影响肿瘤的“变脸”?
既然复发轨迹如此多样,那么是否存在一些特定的因素,会影响GBM的演变方向呢?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两种重要的“分子调节因子”(Molecular Modifiers):MGMT基因的状态和治疗诱导的基因组变异。
首先是MGMT(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它是一种DNA修复蛋白,其启动子的甲基化状态(MGMT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与GBM对TMZ化疗的敏感性密切相关。MGMT启动子甲基化(MGMT-MET)的肿瘤通常对TMZ更敏感,患者预后也更好。这项研究发现,在MGMT启动子甲基化的初发肿瘤中,恶性细胞本身的MGMT基因表达水平显著低于非甲基化的肿瘤(P = 5.3 × 10⁻⁶)。研究进一步构建了一个模型,利用恶性细胞的MGMT表达水平来预测MGMT甲基化状态,发现这种基于表达水平的预测与患者手术间隔时间(衡量治疗反应的一个指标)的相关性更强。
更重要的是,恶性细胞的MGMT表达水平与肿瘤复发时的间充质样(MES-like)状态丰度显著相关。具体来说,在MGMT表达水平较低的肿瘤(通常对应MGMT-MET)中,复发时间充质样状态的丰度会降低;而在MGMT表达水平较高的肿瘤(通常对应MGMT-UM)中,复发时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间充质样状态的丰度升高。间充质样状态通常与肿瘤的侵袭性、血管生成和耐药性有关,因此MGMT-low肿瘤复发时MES-like状态的减少,或许解释了MGMT-MET患者更好的预后。
其次是治疗诱导的基因组变异。研究发现,在复发肿瘤中,一些与DNA错配修复缺陷相关的突变信号(如COSMICv3 SBS签名中的SBS21)增加了,同时还有小片段插入/缺失(small insertion/deletion)的负担增加。研究特别关注了小片段缺失,发现有10例复发肿瘤表现出明显的small deletion phenotype。
有趣的是,那些获得small deletion phenotype的复发肿瘤,与缺氧(Hypoxia)和间充质样(MES-like)细胞状态的富集相关(paired Wilcoxon rank-sum test, P<0.05)。缺氧状态已知与GBM对放疗的耐药性有关。这提示我们,治疗诱导的基因组变异,尤其是小片段缺失,可能驱动肿瘤向更具侵袭性和耐药性的细胞状态演进。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识别出两个关键的“分子调节因子”:恶性细胞的MGMT表达水平(与TMZ反应相关)和小片段缺失变异(可能与放疗相关),它们能够影响肿瘤复发时恶性细胞的状态演变轨迹。
生态的共舞:肿瘤细胞与微环境的协同演进
这项研究还强调了一个重要的概念:GBM的“生态系统”是协同演进的。也就是说,恶性细胞的变化与肿瘤微环境的变化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研究发现,恶性细胞状态丰度的变化与TME细胞构成以及基线基因表达谱的变化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例如,恶性细胞的神经元样(NEU-like)状态与神经元基线表达谱密切相关,这种关联在复发肿瘤中可能增强。同时,胶质-神经TME中的少突胶质细胞和神经元表达的配体(如神经粘连素NLGN和神经调节蛋白NRG家族)被预测与恶性细胞的受体(如神经粘连素家族NRXN或ERBB4)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在复发时可能更频繁。这些发现支持了治疗后残余GBM细胞可能更深入地整合到脑实质中的假说。
这意味着GBM的复发不仅是恶性细胞自身的演变,也是其与周围微环境共同适应和改变的过程。恶性细胞的状态可能会影响它们与TME细胞的互动方式,而TME细胞的组成和分泌的信号也反过来影响恶性细胞的行为和状态。这种复杂的“共舞”共同塑造了肿瘤的复发。
绘制复发“导航图”:通往更精准的治疗
这项大型单细胞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前所未有的GBM复发“蓝图”。它清晰地展现了GBM复发轨迹的巨大多样性和复杂性,挑战了以往某些过于简化的模型。虽然大多数轨迹是不可预测的“迷宫”,但研究成功地在这些“迷宫”中识别出了一些关键的“路标”和“岔路口”。
最普遍的变化是肿瘤生态系统的构成转变:恶性细胞比例下降,胶质-神经TME增加。这或许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并与更好的预后相关。同时,研究也揭示了恶性细胞状态转变的复杂性,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某些复发状态(如间充质样/缺氧)预示着更差的预后。
更重要的是,研究识别出了影响这些轨迹的关键分子调节因子:恶性细胞的MGMT表达水平和治疗诱导的小片段缺失。这些因素似乎能够“引导”肿瘤走向特定的演变路径(例如,MGMT-low与复发时MES-like状态的减少相关,小片段缺失与缺氧/MES-like状态的增加相关)。
这项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它提示我们,GBM复发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过程。理解每个患者肿瘤独特的演变轨迹以及驱动这一轨迹的关键因素,是实现精准治疗的关键。未来,我们或许可以利用单细胞技术和基因组分析,为复发GBM患者绘制个性化的“复发导航图”,根据肿瘤复发时的具体生态系统状态和潜在的演变驱动力,选择最有可能有效的治疗策略。
尽管GBM的复发轨迹复杂如迷宫,但这项研究利用前沿的单细胞技术,为我们点亮了迷宫中的部分路径,为最终征服这个顽固的“脑中恶魔”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的研究将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轨迹的详细分子机制,并开发能够针对特定复发亚型的创新疗法。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