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一处受损,全身皆兵:肾上腺素信号如何为蝾螈的下一次再生“预热”?
来源:生物探索 2025-11-01 09:03
这项发表于《细胞》的研究,从一个出人意料的宏观现象出发,通过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实验,最终锁定了一条完整而优雅的分子与细胞机制。
在再生医学研究领域,墨西哥钝口螈(Axolotl),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六角恐龙”,无疑是明星级的存在。它那近乎完美的组织再生能力,尤其是断肢重生,长久以来都让无数研究者心驰神往。我们习惯于将目光聚焦于那个神奇的伤口,细胞如何聚集,分化,并最终“凭空”再造出一个结构复杂的完整肢体。然而,我们是否忽略了什么?当一只蝾螈失去一条腿时,它身体的其他部分,那些“事不关己”的组织和器官,又在发生着什么?它们是真的“风平浪静”,还是早已在悄然间拉响了警报?
10月24日,《Cell》的研究报道“Adrenergic signaling coordinates distant and local responses to amputation in axolotl”,为我们揭开了一个颠覆性的视角。一次断肢,足以让蝾螈的整个身体进入一种“预备”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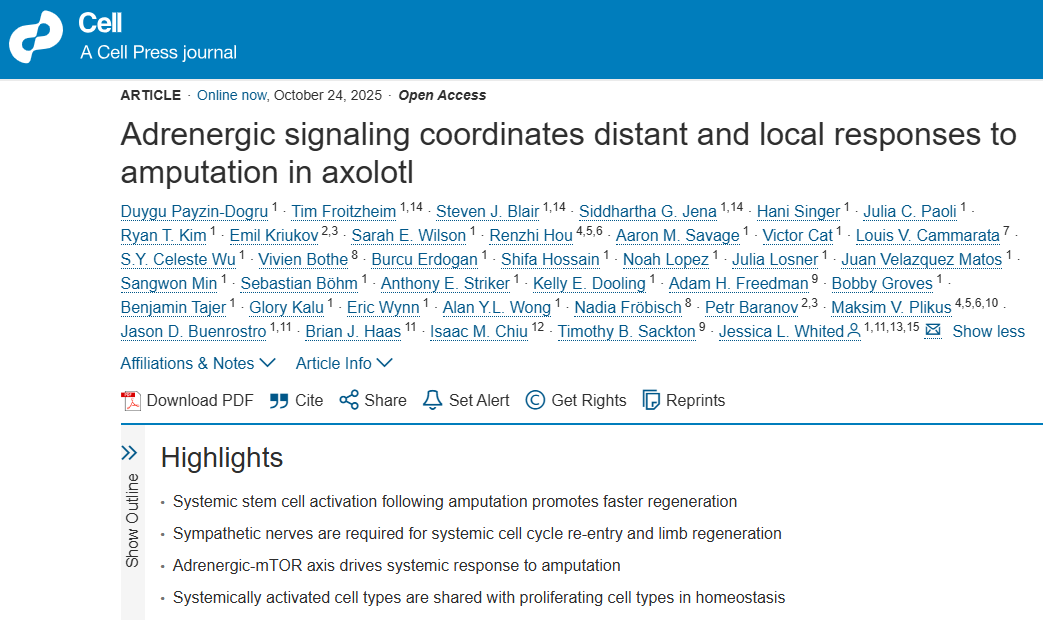
一处受伤,八方支援:再生“预备役”的激活
一场战役的胜利,往往不仅仅取决于前线士兵的英勇,还依赖于后方早已完成的充分备战,那么这场胜利无疑会来得更快、更高效。蝾螈的肢体再生,似乎就遵循着这样一种“全局战略”。
为了验证这个大胆的猜想,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他们将蝾螈分为两组。对于“初始组”(naïve regeneration),他们直接截去其一侧的肢体,然后观察并记录再生过程。而对于“预备组”(primed regeneration),他们则先截去一侧肢体,让身体做出反应。七天后,当这个“全身警报”可能已经被拉响时,再截去其对侧的、此前完好无损的肢体。
结果令人震撼。“预备组”的蝾螈在第二次断肢后,其再生速度显著快于“初始组”。具体来看,在断肢后的第14天,“预备组”肢体末端形成的再生芽基(blastema),即新肢体的雏形,面积明显更大。到了第25天,当“初始组”的许多肢体还在为分化出脚趾而努力时,“预备组”已经有更多个体形成了清晰的趾状轮廓。这就像两支同时开工的建筑队,一支按部就班,另一支则因为所有建材和工人都已提前到位,施工进度一日千里。
为了从分子层面证实这种“预备”状态,研究人员检测了再生芽基中的一个关键基因Prrx1的表达。Prrx1是肢体发育和再生的重要标记。果不其然,“预备组”肢体在断肢后第5天,其Prrx1的荧光信号强度远高于“初始组”,表明它们的再生程序启动得更早、更强劲。
这种“预备”状态能持续多久呢?研究人员发现,这种优势并非永久性的。如果第一次断肢和第二次断肢之间间隔长达四周,那么“预备组”的再生速度就和“初始组”没有区别了。这说明,这种全身性的动员是一种相对短暂的、为应对短期内可能发生的再次伤害而存在的应急机制。
那么,这种机制在自然界真的有意义吗?毕竟,实验室里的连续断肢听起来有些“残忍”和极端。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野外。他们观察了蝾螈的近亲——虎皮蝾螈(tiger salamanders)的自然种群。在一个户外池塘中,他们发现许多虎皮蝾螈的身上同时有多条肢体处于不同的再生阶段。这意味着,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确实会接二连三地遭受伤害,比如来自同类的啃咬或天敌的捕食。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下,第一次受伤后能让全身“打起精神”,为下一次可能的伤害做好准备,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演化优势。
这个发现本身已经足够惊人,但它立刻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远方的肢体是如何得知另一处发生了创伤?这个跨越身体的“警报”信号,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的?
神秘的信使:是谁在全身传递“警报”?
在生物体内,能够实现长距离、快速信息传递的系统,我们首先会想到两个:一个是遍布全身的血管网络,通过循环系统输送激素;另一个就是如同信息高速公路般的神经系统。
研究人员首先将矛头指向了神经系统。他们进行了一项关键实验:在一组蝾螈中,他们通过精细的手术切断了通往右侧肢体的神经束(denervation),使其“与世隔绝”;而在另一组(sham-operated)中,他们只做了切口但并未切断神经,作为对照。随后,他们截去了所有蝾螈的左侧肢体。
14天后,当他们检查右侧肢体内的细胞增殖情况时,答案揭晓了。对照组的右侧肢体中,细胞增殖(通过EdU标记检测)水平如预期般显著上升,全身动员令成功下达。然而,在神经被切断的那组,右侧肢体的细胞增殖水平毫无变化,仿佛对远方的创伤一无所知。
这说明,信息的“接收端”必须有完整的神经系统。那么,“发送端”呢?研究人员又做了一个反向实验。他们先切断左侧肢体的神经,然后立刻截断这个刚刚“失联”的肢体。结果,对侧的右肢也未能启动细胞增殖。这证明,创伤信号的发出,同样依赖于受伤部位的神经系统。
至此,一幅清晰的图景浮现出来:肢体截肢的伤害信号,由受伤部位的神经传入中枢,再由中枢通过神经系统传出,指令远端组织做好准备。这是一条完整的、需要两端神经都保持通畅的“军用专线”。
神经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具体是哪一部分在执行这个任务?研究人员推测,断肢这样剧烈的创伤,很可能会激活身体的应激反应系统,也就是由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主导的“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反应。交感神经遍布全身,能够快速调动身体资源以应对紧急情况。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他们使用了一种名为6-羟基多巴胺(6-OHDA)的神经毒素。这种化学物质能特异性地摧毁交感神经末梢。当他们给蝾螈注射6-OHDA,破坏了其交感神经系统后,再进行断肢手术,奇迹消失了。远端肢体的细胞增殖反应(systemic activation)被完全抑制。
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就连受伤肢体本身的再生也受到了严重阻碍。没有了交感神经的参与,再生芽基的形成变得异常困难,尺寸显著小于对照组,并且芽基内的细胞增殖率也大幅下降。这个结果意义非凡。它不仅证实了交感神经系统是传递全身“警报”的关键信使,还揭示了它在局部再生中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提示我们,交感神经系统可能通过某种信号分子,同时在“远方”和“前线”执行着不同的任务。
那么,这种信号分子究竟是什么?它的“语言”又该如何解读?
肾上腺素信号的双重“密语”:远方“动员”与近处“集结”
交感神经系统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其末梢释放的一种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这种分子会与靶细胞表面的肾上腺素能受体(adrenergic receptors)结合,从而引发一系列生理效应。这些受体主要分为两大类:α受体和β受体。
会不会是不同类型的受体,在解读着这同一份“动员令”的不同含义?研究人员利用药物学工具,开始“窃听”这场分子对话。他们首先使用了一种叫做育亨宾(yohimbine)的药物,它是一种α2-肾上腺素能受体的特异性拮抗剂(antagonist),能够阻断去甲肾上腺素与这类受体的结合。
当用育亨宾处理蝾螈后,他们发现远端肢体的全身激活反应消失了。不仅如此,当他们进行“预备”再生实验时,育亨宾同样让“预备组”的再生加速优势荡然无存。这表明,远方的组织正是通过α2受体来接收“警报”,并进入“预备”状态的。
接着,他们换用了另一种药物,普萘洛尔(propranolol),这是一种广谱的β受体拮抗剂。这一次,结果截然不同。普萘洛尔处理过的蝾螈,其远端肢体的全身激活反应完全正常,细胞增殖水平与对照组无异。然而,当研究人员观察受伤肢体本身时,却发现其再生芽基内的细胞增殖受到了严重抑制。
一个优雅而清晰的结论诞生了:交感神经释放的同一种信号分子(去甲肾上腺素),通过两种不同的受体,巧妙地实现了“区域化管理”。 在身体的远端,组织细胞通过 α受体 接收信号,启动全身性的细胞增殖和“预备”程序。而在受伤的局部,“前线”的细胞则通过 β受体 接收信号,驱动再生芽基的形成和生长。
这就像一位指挥官用同一个指令,让后方部队(远端组织)进入战备动员(α受体介导),同时让前线部队(局部组织)发起冲锋(β受体介导)。研究人员甚至更进一步:既然我们知道了“动员”的口令,我们能主动发出这个口令吗?他们使用可乐定(clonidine),一种α2受体的激动剂(agonist),来模拟信号。结果发现,即使在没有“预备”过程的单次截肢中,可乐定的使用也显著加快了肢体的再生速度,完美复现了“预备”状态的效果。
至此,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从宏观现象追踪到了具体的信号通路。但故事还没有结束。信号已经接收,细胞内的“引擎”又是如何被启动的呢?
启动细胞的生长引擎:mTOR通路的关键角色
在细胞生物学领域,mTOR(mechanistic target of rapamycin)信号通路是调控细胞生长、增殖和代谢的核心枢纽。它像一个总开关,整合来自外界的营养和生长因子信号,决定细胞是“休养生息”还是“开足马力”生长。
研究人员自然而然地想到,肾上腺素信号引发的如此广泛的细胞增殖,会不会正是通过激活mTOR通路来实现的?他们使用雷帕霉素(rapamycin),一种mTOR通路的经典抑制剂,来验证这个假设。实验结果非常干脆利落:雷帕霉素几乎“冻结”了整个再生过程。无论是受伤局部的再生芽基形成,还是远端肢体的全身激活反应,亦或是由此带来的再生“预备”效应,全都被雷帕霉素有效抑制。
这有力地证明了mTOR通路是整个事件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它与上游的肾上腺素信号是什么关系?它是被后者所调控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检测了细胞内mTOR通路活性的一个关键指标,核糖体蛋白S6的磷酸化水平(pS6)。pS6水平越高,代表mTOR通路越活跃。
他们首先用α受体拮抗剂育亨宾处理蝾螈。结果发现,无论是在远端的未受伤肢体,还是在局部的再生肢体中,育亨宾都显著降低了pS6的水平。这说明,驱动全身激活和局部再生的α受体信号,确实是通过激活mTOR通路来发挥作用的。随后,他们又用β受体拮抗剂普萘洛尔进行了同样的实验。这一次,只有局部再生肢体中的pS6水平被降低了,而远端肢体则不受影响。
这些数据完美地串联起了整个信号链:断肢 → 交感神经激活 → 释放去甲肾上腺素 → 远端α受体/局部β受体激活 → mTOR通路激活 → 细胞增殖与生长。
为了提供更直接的证据,研究人员还在体外培养的蝾螈成纤维细胞(AL-1 cells)中进行了验证。当他们向培养皿中直接加入肾上腺素时,细胞内的pS6水平迅速飙升,证实了肾上腺素信号能够直接激活细胞的mTOR通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清晰的信号传导路径。但一个新的谜题又浮现出来: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全身动员中,被唤醒的究竟是哪些细胞?这些响应号召的“预备役士兵”,是何身份?它们又是如何被“训练”成再生先锋的?
揭秘“预备役”身份:平时是“工兵”,战时成“先锋”
要找到这些被激活的细胞,首先要把它们从数以万计的“沉睡”细胞中分离出来。研究人员利用了流式细胞术(FACS),正在增殖的细胞,其DNA含量会翻倍(从2C变为4C),通过对DNA含量进行染色,研究人员成功地将这些处于4C状态的“活跃”细胞(即全身激活细胞,Systemically Activated Cells, SACs)分离了出来。
通过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技术,他们得以逐一解读这些细胞的“身份档案”。结果发现,这些SACs并非某种神秘的、专为再生而生的休眠干细胞。恰恰相反,它们与那些在正常生理状态下(homeostasis)为了组织生长和修复而进行增殖的细胞,属于完全相同的类型。它们是成纤维细胞、肌肉卫星细胞等,是身体组织中一群默默无闻的“工兵”和“维修员”。
这意味着,蝾螈的再生策略并非依赖于一小撮“特种兵”,而是通过一个全局性的信号,动员了大量平时就在岗的“普通士兵”,赋予它们新的使命。那么,这种“新使命”是如何被赋予的?仅仅是让它们多分裂几次吗?研究人员怀疑,这种“预备”状态可能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改变——表观遗传(epigenetic)层面的“重编程”。
他们运用ATAC-seq技术,分析了不同细胞群体的染色质开放区域。染色质的开放与否,决定了哪些基因能够被读取和表达,是细胞身份和功能的重要调控方式。当他们比较“预备役”SACs、正常增殖细胞和真正位于再生芽基中的“精英”细胞时,一个惊人的发现出现了。SACs的染色质开放模式,与再生芽基细胞惊人地相似!它们共享了多达95个在正常增殖细胞中并不活跃的转录因子结合基序。
更重要的是,这些被提前“解锁”的基因区域,富含调控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过程的关键转录因子(如Twist, Snai1, Egr1)的结合位点。EMT是细胞获得迁移能力和可塑性的关键过程,在胚胎发育、伤口愈合以及再生中都扮演着核心角色。通过精细的RNA原位杂交技术,研究人员在“预备”肢体的多种组织中,包括皮肤、肌肉和骨骼周围,都观察到了Snai1等EMT相关基因表达的显著上调。
至此,谜底的最后一块拼图被找到。所谓的“预备”状态,其本质是一种深刻的表观遗传学上的“启动”(priming)。远方的创伤信号通过神经-肾上腺素-mTOR轴,不仅唤醒了远端组织中的祖细胞让其增殖,更重要的是,它提前打开了这些细胞基因组中与“再生”和“可塑性”相关的“篇章”。这些细胞虽然还在原地,但它们的内在状态已经发生了质变,从一群按部就班的“工兵”,变成了一支蓄势待发、随时可以投入战场的“先锋”。一旦该部位真的受伤,它们就能比“未经训练”的细胞更快地响应局部信号,迁移、分化,并构建新的组织。
从“一隅”到“全局”:再生医学的新启示
这项发表于《细胞》的研究,从一个出人意料的宏观现象出发,通过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实验,最终锁定了一条完整而优雅的分子与细胞机制。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再生的传统认知,将研究的视野从受伤的“一隅”拓展到了整个有机体的“全局”。
我们现在知道,蝾螈的断肢再生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场由交感神经系统总指挥,通过肾上腺素信号进行远程调度,以mTOR通路为执行引擎,最终在表观遗传层面完成对全身祖细胞“战前动员”的复杂生命过程。
这一发现的意义,远不止于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它为我们思考人类的再生潜能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人类无法再生肢体,但我们体内拥有与蝾螈完全相同的交感神经系统、肾上腺素信号和mTOR通路。我们的细胞在受伤后,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但微弱得多的全身性反应?我们能否通过药物或其他手段,模拟蝾螈的这套“动员令”,去“唤醒”我们体内那些沉睡的再生潜能?
例如,在面临严重创伤(polytrauma)或需要大面积组织修复的病人身上,是否可以通过调控肾上腺素信号通路,来提升全身组织的修复能力和对手术的响应速度?这些过去看似科幻的设想,在这项研究的启发下,似乎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当然,前路依然漫长。中枢神经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角色是什么?这个“预备”状态又是如何被精准地“关闭”以避免资源滥用?这些都是未来亟待解答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项研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生命的奇迹,往往隐藏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却从未深入探究的联系之中。
版权声明 本网站所有注明“来源:生物谷”或“来源:bioon”的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于生物谷网站所有。非经授权,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取得书面授权转载时,须注明“来源:生物谷”。其它来源的文章系转载文章,本网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转载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


